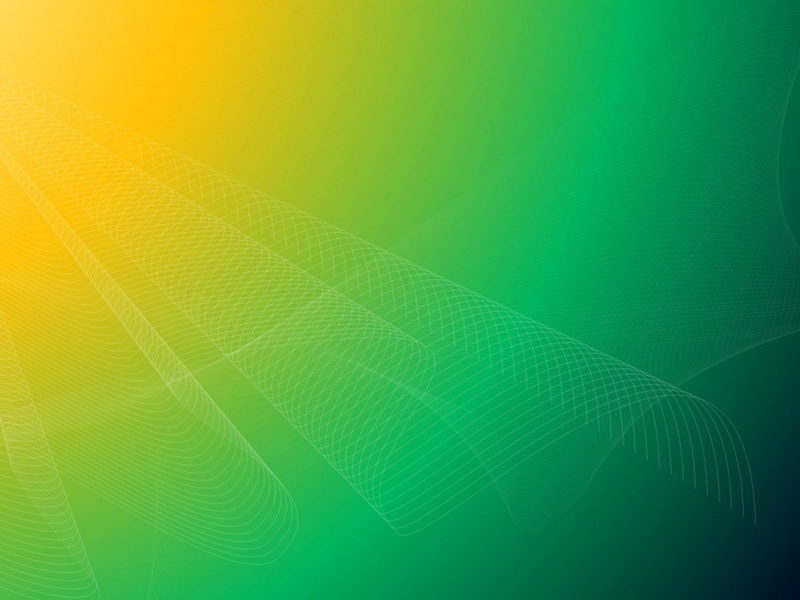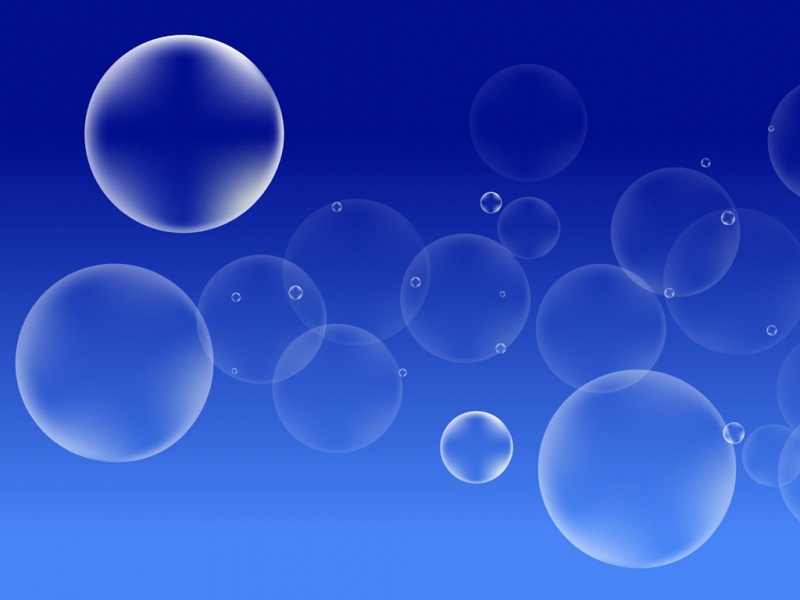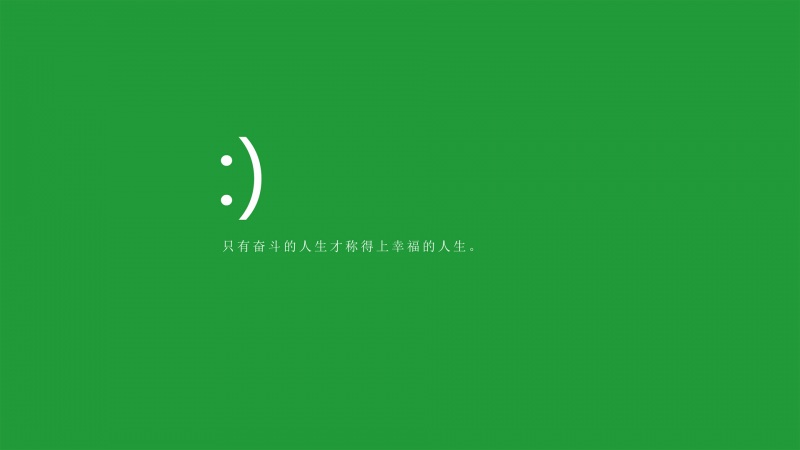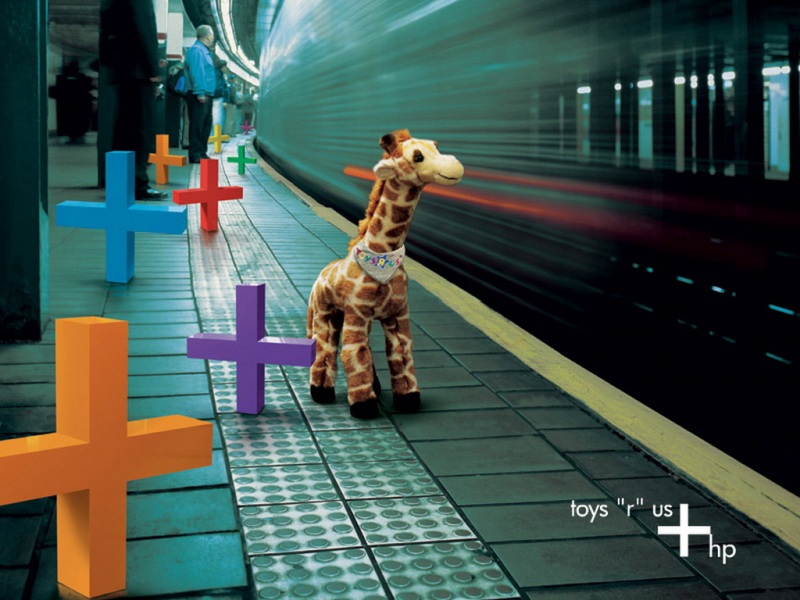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0586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2 分钟。
6 32 0 1 5西部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唐 娜 马知遥摘 要: 以陈兴华为代表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演述人东郎,千百年来坚守和传承史诗《亚鲁王》的文本与信仰,并用身心融入、力行史诗的演述传统,他们是地方性知识的持有者和传播者。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东郎生活在压抑和歧视的氛围中,他们的遭遇和处境的种种变数,深刻影响了史诗的传承行为。史诗传统如要获得宽松、可持续的传承环境,需要主流社会为东郎“正名”,东郎群体的话语权的设立以及社会身份的确立,是保护史诗有效传承的前提与根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无疑有效推进了这一进程。关键词: 东郎;亚鲁王;传承;演述传统文章编号: 1003 2568 (2015)03 0068 06 中图分类号: I276.3;G122 文献标识码: A作 者: 唐娜,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邮编:300072马知遥,博士,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邮编:300072※访谈对象:陈兴华,男,苗族,生于 1945年,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猴场镇打哈村打望组人,苗族史诗《亚鲁王》歌师。自 1964年起,为本村村民及周边区域参加和主持葬礼,唱诵《亚鲁王》,坚持至今。2012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访谈整理者:唐娜马知遥一、陈兴华的东郎 ① 生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亚鲁王是苗人的皇帝,是苗人的祖先,是一个英雄,一个了不起的人,老的就讲一定要继承亚鲁王,做哪样大事小事,一定不能违背亚鲁王的精神。在史诗《亚鲁王》里面人们就是称呼亚鲁为王的,他是我们这支苗族的祖先,经过千辛万苦带着苗族的子民一步步走过来的。亚鲁王虽然是个大人物,也不是顺顺利利的。之所以会定居在麻山,因为当时各方面势力和在计策当中有些失策,讲丑一点就是失败了,就往这些偏僻的地方搬,就是这个样。我苗族之所以这么尊敬他,崇拜他,因为他真正是个英雄,在那种战争年代,灾难时期,他能够坚持下来,一直跑到贵州这个地方来发展,是很不容易的。小时候我听那些老年人唱《亚鲁王》,讲开天辟地、造人、造山的故事,都觉得很有意思,那时起我就想,以后一定要继承他(图 1)。我是(19)45年 ② 生的,家住在猴场镇打哈村,打哈村有将近两百户人,住得分散不集中,我是打望组的,打望组只有十五六户人家,不到一百人,人均土地占不到一亩,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图 2)。我小的时候生活是难一些,那个地方就是岩山,连基本的泥土都没有,所以生活是非常困难。粮食是少得可怜,玉米饭有时都没有得吃,更不用说肉,以瓜和野菜为主。养鸡、养猪的都没有,没有粮食,养殖业根本搞不起嘛。原来还交公粮, (19)79年以后国家扶持就不征收任何粮食了,还进行补贴,我们在紫云县来讲是最图1《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段新培/摄)写在前面:对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的访谈,是在跨越族群、语言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围绕的内容却是西部苗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信仰和口头传统。因此在对某些话题的交流上是困难重重的,仅从《亚鲁王》的名称来看,虽然这一庞大的口头诗篇被学界认定为英雄史诗,但是在歌师生活的苗语世界中,它是丧葬时唱诵给亡人的叮咛,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汇,因此歌师不断使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和指代,对于其他更加深入的苗文化事项更是如此。然而,笔者又是十分庆幸的,在经过半个月的麻山田野调查,发现因常年沉浸苗文化中,苗寨中多数歌师是无法与外界通畅交流的,而本文访谈对象陈兴华老人作为退休公职人员,既有汉语言的优势,更宝贵的是他作为麻山苗人一员对族群的情感认同、对亚鲁信仰的长年坚守,以及对于史诗传承责任的勇敢担当,是一位让人敬仰和名副其实的国家级传承人。①东郎,苗语音译,即歌师的意思。②文中访谈对象对提及的时间采用简述的方式,为确保符合学术论文编辑规范。笔者对其加注具体年份,下文同。※非物质文化遗产68DOI:10.16564/j.cnki.1003 2568.2015.03.01262 0 1 53西部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穷 的 一 个 村 。我们村(20世纪)90年代 通路 ,2005年 才通电,通电以后有了电视看,大家高兴得真是无法形容,还有很多家买不起电视,直到现在也还有部分没得。我兄弟姊妹六个,小的时候家里面条件差得很,我们都读不起书,那个时候学校在猴场镇,我家隔学校很远,有十多公里。(19)58年的时候,我们也来报名上学,不是为读书是为了混生活,吃饭随便到哪边都有饭吃的,晚上到哪边就在哪里歇,就是这个样。可是最后读不成,搞大跃进学校都关门了, (19)58年来入学,一年都认不到老师是哪个,都是在搞大跃进,搞生产。我们背着书包就混了这么一年,一九五九年年纪大了就下放回家去了。(20世纪)60年代初搞扫盲、学文化,有认字课找会写字的人来把它写起,我就跟着大家学,我认得以后就去教别人,搞“半耕半读”,我就是这样子出来的。那时候国家每年都来征收粮食,每年都请人去协助收粮,我就给他们请去。那时我将近三十岁了,搞粮食工作时连汉话都讲不清楚,但是因为我老实又做事认真,后来就被他们留下来,成了公家的人,一直做到退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十五六岁,对《亚鲁王》特别感兴趣,但是不敢去碰。当时这是受反对的,定位牛鬼蛇神、封建迷信,(19)58年就大张旗鼓地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开路 ① 完全不允许搞,是要被批斗的。一些老的歌师被抓起来,还要把脸画乱,搞一个尖尖帽戴上,挂个牌牌在村子里面游街,说搞封建迷信就要丑化。大家都很害怕,因为是很丢脸的事。虽然文化大革命这么凶,但是我们老的讲要继承、遵循亚鲁王,办丧事也好,红喜事也好,样样都要来祭奠他。上面不让搞,下面办丧事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办,做得简单一点。从前没有限制的时候人一死就开始唱,一直唱到上山,听老人讲要个把星期才把这些履行完了。当时那个环境偷偷地做,必须要压缩,基本的框架有,能省略的省略,能简化的简化,只有一个晚上了。(19)61年的时候不搞大集体了,各家各户分成小组搞生产。这样就有时间了,那些老年人都爱集中,他们闲着的时候就摆、讨论亚鲁王的故事,我就跟着他们到处走,就随意跟着学。当时村里面歌师还是很多,每个家族都有,因为做丧事的时候,有一个段落是唱自己家族的,其他家不能代替的,所以必须家家都有。光我家就一个堂伯、一个母舅,另外还有个伯岳父,他们三个人都会。我小的时候就跟着他们到处跑,跟着他们学,开始的时候没有哪样规则,光是看热闹,到(19)64年我们就认认真真学了,后来学成就参加进去了。因为都是亲戚,我没有正式地拜师父,其他的就要拜了。我捡这点便宜,确实没有花费过哪样。开始我跟堂伯和母舅学习开路,学到一点,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左右,我是偷偷去学,心里是很害怕的。有次去参加他们老的丧事,那些老的都被抓了,我们小所以他们不晓得抓我们。(19)64年他们就带我正式参加丧事,以听为主,我已经能唱一部分了。开始学的时候都还没有要在丧事上唱的想法,到参加了以后才觉得丢不下。学了就要唱,越来越觉得唱得满有道理。我第一次在丧事上唱《亚鲁王》也是在(19)64年,那个葬礼很简单,当时在我们猴场还都是受限制的。老的带我们去,给我交待你唱这一节。还教我说不能加很多语言,怎么怎么唱。我唱的时候很紧张的,当时听那些老年人摆的说这个东西太神秘了,心里头还是很害怕的。怕有哪样履行不到的,怕得罪亡人。我那第一次唱不出来,明明已经全部念完(学会),进去一唱又全部模糊。因为害怕,虽然唱的是简单的部分,但是心头一紧张,就唱不出来了。我恼火,停一停,慢慢想一下唱。还是多经历以后才能慢慢地把握这些东西,胆子逐步逐步也大了。到(19)65年,我基本上就全部掌握了,但是偷偷摸摸不敢讲。到(一九)七几年,我可以安排葬礼了,就是我已经有权力和号召力去召集其他人了。因为我以前是记工分的,有一点知识,所以大家比较听我的话。我(19)69、 (19)70年这个阶段开始主持葬礼,直到退休以后还在做,在粮食系统工作几十年,身边没有人知道我是搞开路的,我一点都不敢说,因为搞不好就把饭碗给丢了。但是我不去这桩事情就办不下来。我们村里面也有别人能开路,但是知道得不全面,一个人掌握一部分,我如果不回去,他们做不起来。每次我是偷偷摸摸地去,一下班就走,但是到下面去还要走许多路,找几个人在那里先稳着,有时晚上半夜我才到。第二天天没亮,我把该办的事情办了,就交给他们了,我又赶回来上班。这样做辛苦是图 2 紫云麻山地区的喀斯特地貌①开路,苗族丧葬仪式之一,即将亡人带入归去之路。开路过程中要唱诵史诗《亚鲁王》。696 32 0 1 5图 3 2012年陈兴华歌师在人民大会堂《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展演史诗唱诵(段新培 /摄)辛苦,关键是提心吊胆的,怕被别人发现国家干部还搞这个东西。我曾经有两次差点被发现。当时抓牛鬼蛇神,抓封建迷信,不管什么单位全部参加,各行各业都要投入,安排去参加工作组。听说有人在办丧事了,就组织一个工作组去抓,我也是国家干部,政府一声号令,单位安排人参加,我不能拒绝。我是搞开路的,工作组的人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喊我不干也不行,所以就得跟着去。遇不到最好,假如避不开,我不抓他们,他们就要抓我了。就像搞现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整天去乡下整,但是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当中也有违反计划生育工作的。他去抓人家,回来人家又抓他,这个现象很多。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心情实在是难,假如真的遇到人家在办,该怎么办。到时 候 人 家 抓我,我的饭碗也保不住了。那个心情真的是太复杂了,当时只要一听到什么“运动”,心里就很难受(图 3)。我差点被抓的这次就是我们单位参与的工作组,我唱的时候就安排人在那里看守,发现工作组来了,我就赶快跑了,狼狈得很。这一回还是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去的,叫杨秀文,也是苗族,但是我看到他来了就跑了,真是难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还有其他人,他也不会为我说话的。我其实很幸运,也很不容易,偷偷摸摸开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被他们看见过。经常下班就溜去,天不亮就来了,多半时间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办公室也有人知道我在说假话,但是他们不讲,因为也不清楚我在搞什么,拿不出什么依据。我一辈子在单位因为这件事说假话太多了。有些人也在骂我过,参加工作还搞这些,太不相称了,有的说到时候饭碗也要砸丢了。说实话我也想过,没有想过就不这样注意了,平时说话这些都不提也不说,不议论这些东西,装不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个时候一旦被人发现了,开除了我,体力劳动我搞不来的,所以这个饭碗很重要。可是对我来说不搞这个也不行,我在那个年代还是很注重这些东西的,丢不下了。我们那里的人办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我们是亚鲁王的子孙后代,我们要继承亚鲁王的传统,几乎是天天都在说这些,所以我必须要继承亚鲁王的。而且,我做的这些,都没有白做。做东郎的人,大多数家里都条件不好,因为他们只钻研亚鲁王这些东西,不想找钱这些。我家遭的一次火灾对我家影响很大。(19)7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寨子着火,全部烧得一样不剩,大家都无家可归了。幸好我们寨子人数不多,只有七八户人家。在火灾之前我是(19)78年才做的房子,造房子把家里的钱都用光了,只有一年时间就烧了。着火以后我们在洞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行了,我带我父母到猴场镇上来住。镇上住的都是汉族,他们语言不通,呆不下,又到亲戚家住,一家住一段时间,这么过来的。一直到(19)85年,我才又修房子。当时没有钱,爱人不能劳动,遭火灾之后,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受刺激了就疯了,家里有四个孩子,我的精神负担不是一般的大,那个时候太难了。但是因为我在给大家开路,为大家服务,只要说一声,或者人家知道你今天要办什么事情了,都主动来帮忙的,否则我就过不到今天。虽然像一栋房子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价值,但是要有人力,做的时候是花费代价的。我们那里没有木材,到处去买木头,交通不便,要人工去抬,那时候也没有路,非常吃力。所以我的房子的造价是算不出来的,自己花不多,也没有什么钱,有部分材料是买的,大部分是这家送一颗那家送一颗这样来的,劳动是大家来帮忙的。有的人是我去喊他来,大部分是没有喊的,听说我家做什么,就主动来帮助。人家来帮忙,我家应该给他们做饭吃,有的人家不吃饭把活做完就回去了,有的人家是吃了饭才来的,是这个样子把房子建起来的。他们有的人开路是讲钱的,一场是多少钱,直到现在我就不讲,我为什么不讲,因为我已经得了。二、史诗《亚鲁王》的演述传统当时我们学唱《亚鲁王》的时间还要限制在正月间,一般都在晚上,其他时候师傅也不教你。他说平时如果乱唱,庄稼不成熟啰,人们不安宁啰,所以就只能在正月间。正月间把老祖公都请来家,才可以讲。其他地方七月也勉强,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七月都不让,所以平时都很少念这些东西。为哪样现在的人逐步懂得少哩,就是有这么个忌讳,不得一定的场合不允许到处乱唱。一年只用正月来学,时间是很少。平时要学这个东西,可以指导程序,不用唱的形式,用摆故事的形式讲,比方讲亚鲁王生平的故事,就像砍马 ① 、开路那些内容平时都不允许讲,必须在①砍马,即砍马经或称开马路,传统丧葬仪式有砍马环节,这一部分在砍马仪式中唱诵。非物质文化遗产7062 0 1 53正月里面,或者有丧事的时候。教我的这三个人,我家堂伯叫陈老幺,我家母舅叫韦昌秀,我家伯岳父叫伍老乔,这三个都厉害。伍老乔他教我落地方 ① 这一部分,是最不好记的,人名、地名多,特别拗口。陈老幺教我的是亚鲁祁 ② 这部分,这部分有故事情节,很有意思,而且又好记,我最早会唱的。我舅舅教我的是开路仪式这部分,包括唱词和履行这些的时间,比如办丧葬哪个时间必须要发出去,哪个时间必须要下葬。这些时间要根据当天的黄道时、黑道时,就牵扯到汉文化。汉文化的东西很早就到我们风俗里面了,也可能苗族文化和汉文化是同时产生。我舅舅韦昌秀他有点文化,这些是他教我。但是砍马的部分,我没有学,因为我们不兴砍马,猪经和鸡经 ③ 的部分都学了。很多歌师没有学砍马那块,因为耗费很大。现在四大寨乡砍马最多,四大寨虽然不富裕,但是解放以来,政府对四大寨一带还是相当照顾的,他们都是少数民族,苗族占绝大多数,政府当时对他们反对就少点,所以这个风俗他们就继承下来(图 4)。砍马道理我晓得,但是我们陈姓祖宗不砍马,砍马还是要比较富裕的人家,我们祖祖辈辈下来都很穷。后来经济方便了,也不去做了,老年人都没有兴,我们就不再来了。我们叫“有礼不可灭,无礼不 可 兴 ”,已经 灭 去 了 就不再兴了,就是这个样。当 时 我们有三四个人一起学的,最后学会的只有我和我家一个兄弟。学不会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因为唱有困难,一个是害羞,不好意思开口,一个是会讲内容调子不会唱,有些掌握不准唱着唱着自己唱不下去了。还有的人记不到,首先要把内容了解认识清楚了,要是只凭记是记不了好多的。我自己的父亲和亲兄弟也跟着学过,但是没有学会,还是唱不成。我学会了我父亲还是很高兴的,哪个学懂了亲戚房族都高兴的,因为自家得用。学的时候要分段落,有程序的,先把主干掌握了,然后根据情况来加内容,不能超越这个主题。内容分有几种情况,时间上一般办这场丧事是好久时间,再看如何来掌握,内容不能丢,但又不能超过这个时间,这个就很难了。以前在停丧的期间非常长,可以用几天几夜的时间来唱,现在就用的时间非常简短。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唱一晚上,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这么一来,尽量能简化就简化,歌师唱也唱不齐,就把最精简的那一部分唱出来,不怎么紧要的地方就把它省略了。但是深入掌握的人才会灵活应变地缩短,假如不灵活的、不清楚的只有照本来的唱,一晚上都念不完。时间跟不上,不能在规定时间发丧的话,对孝家不好,对东郎也不好。既要赶到这个时间,内容又要齐全,这个难度大。对于经验不太丰富的东郎,他不知道如何缩小缩短,假如对于内容掌握不全面,他就不敢这样去处理。所以现在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唱不去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唱《亚鲁王》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偏重的内容不一样。有的地方注重创世的部分, “惑”或“眉”④的内容。我们那个地方偏重于亚鲁王的 12个儿子,通常注重的是他某一个儿子的征战故事。亚鲁王儿子和子孙后代多,后人为了继承他,就要唱他的脉络。在我们那个村里面有那么多姓氏的,他们继承的是哪一个儿子,就着重讲这方面的内容,其他的都省略了。所以传到下一代的时候内容就失落一些了。比如我们姓陈的就着重陈姓这一方面内容,以及我们附近这些姓,其他方面我们就很少注重了。我们在唱述的时候,如果我们陈姓的亲朋在场,就关系到自家该怎么唱,我们就注重一些,讲细一点,但是当对方不在场,这方面我们就唱得少了一些,点到为止。在场的这些人,我看到他是谁,无论哪家,我就要唱到他那个家族老祖宗的故事,唱不到就不好。所以在现场唱的时候,各个唱得都不一样,在我的思想观念当中,只要唱出陈姓一些主要人物,时间段落没有多大出入,这就是正确的。所以前来调查的人,这次去听和下次去听就有出入,或者平时在唱和正式在唱有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这么多年我办的丧事数不清多少桩,年把十桩八桩也有,年把两三桩也有,有时候一个月几桩也有,没有规律。我在我们打哈村开路比较普遍,也有在周围几个村,比方马寨村、打哈村、打捻村,另外还有茅坪四大寨的一部分。最远我到过望谟县,离我家①落地方,苗族史诗的一部分,即麻山苗人在麻山山区落地、发展的历程,实为当地的口传家谱。②亚鲁祁,苗族史诗的一部分,由围绕亚鲁的出生、成长、征战的一系列故事组成。③同样应用于杀猪和杀鸡祭祀亡灵的仪式。④涉及苗族信仰文化中各种鬼神的由来。图 4 紫云麻山苗人葬礼中的砍马仪式(段新培/摄)西部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716 32 0 1 5图5 正式的丧葬唱诵现场三十多公里,因为我们有家族在那边。他们亚鲁的这部分不晓得我去帮忙。在我们那个地方不光是我们陈姓的去世我去开路,伍姓、吴姓、韦姓我也去,但是我去我只履行主要的部分(图 5)。特别到最后送亡灵上路的部分神秘一点,一点都错不得,所以个个都怕唱诵这一段。因为一唱这一段,好像是深入到里头去,还是有点神秘的。那一段有几个地方叙述遇到什么东西,过程中是会有点怕的。唱这段胆量一定要有,而且要经验丰富,非常流利。比方我主持葬礼,这一段一定由我来唱。如果唱到中间突然忘了,或者胆战心惊恍惚了,别人不会再替你,只有你自己去应对,葬礼结束以后还要为自己做一场类似法事来给自己解虞。有的人通过这样一搞太紧张,神经就错乱了。我没见过,但是听说过。听老人讲过,看到那个祭祀亡灵的灯光,逐渐离你远去的话你最好是停止不要唱,一唱的话进入魔境就无法出来。我经历过一次,开路的时候,屋头有点一个灯,就在棺材的角角,站起唱的时候,灯就在我前头,看得清楚的。后来我觉得这灯离我慢慢、慢慢地远,越远越小,我休息一下把自己稳住,先心头默念,熟悉以后又唱起来。到熟悉以后,我就要唱这一段, “我离你逐渐远了,我讲你听得到,你望我望不见了。我要隔山隔水地跟你讲,该你去的你要去了,我已经去不到了。看你穿的是布鞋、草鞋,样样你都走得到,我穿的是铁鞋,我过不了江过不了河。”唱这些意思是“现在我们隔开了,你走那边去,我走这边来。”我一共遇到两次这种情况,连他的名字都恍惚了,印象很深刻。我的经验就是看到灯在你面前越来越远之后,一定要有胆量,马上要采取措施来稳住自己的心,回来以后我没有给自己解,胆子还是有点大。其实当东郎挺耗身体,在唱的时候如果你不会缓和声带就唱不下去了,挺吃力的,另外唱的时候要站很久,精力也要特别地集中,很累的。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就得坐下来,站一晚上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些是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被气氛感染自己也要哭起来。有时我就跟孝家说,你们不要哭,因为你一哭我就唱不下去了。比如唱到亡人本身情况,把他交给老祖宗的时候会很伤心,还有唱到亚鲁王吃败仗了那种情景也唱不下去,人家在后面追击,挺惨的,我唱十次有九次要掉泪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是特别适合当歌师,因为我没有出息,不能胜任这样的场合,我每唱一次都坚持不下来,都落泪了。三、史诗《亚鲁王》的整理与传承“文革”后办丧事还是慢慢公开起来了。只是胆子大一点的才做,一看办这桩丧事没人来限制,第二桩就起来,慢慢这样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公开办丧事。可是丧事恢复以后跟原来还是不一样了,比过去简化很多了。因为还是有顾虑,不可能恢复到以前。虽然没有谁来干涉,还是害怕的,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不限制了,还是没说这是正确的。现在随着时代改变,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当时的一些礼仪、礼节,可以说是时过境迁,影响最大的还是人们的观念。我们那个村里面会唱《亚鲁王》的人不多,只有我教的几个。从前大家都还认为是憨包的人才去学。因为去开路没得哪样待遇,又很辛苦的,现在社会每个人都在抓经济,你做这个大家都认为你真的憨得很,笨得很,没有本事,没有经济头脑才去搞这些东西。2009年开展歌师普查的时候,观念转变的人还少,包括乡镇干部大部分对这个东西还在反对的,因为反对开路已经几十年了。乡镇、县城里的干部毕竟是汉族人多,不会容纳我们的亚鲁王。如果整个县城都是苗族的话,那么就不一样了。普查效果不太理想,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乡镇干部还在怕,歌师就更害怕,搞不好要遭殃,被批斗,受歧视。但是一时之间,谁也解释不清楚。我认为《亚鲁王》确实是很重要,只能在心里头晓得,叫我用语言解释不清楚,我无法去说服人,无法去强制哪一个来理解。但是我理解他们,从前我会这个东西,我爱这个东西,但是连念都不敢念。如果说有一天《亚鲁王》失传了,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灾难,一定是大的灾难。在我们这个地方,假如一个老年人去世了,不履行这样的规矩、仪式,亲人的心里面负担很重,精神压力特别重。老人回不到老祖公那里,不知造成后果怎么样,但是亲人的思想压力太大。在我们苗人当中,不这样做就不行。因为怕《亚鲁王》失传,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冒了一次险,偷偷摸摸地录过这个东西。虽说那个年代不限制了,但是当时情况不好,大家还是提心吊胆的,传的也不想传了,学的也不想学了,那时候我就很怕它传承不下来。(19)82年或者(19)83年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堂兄弟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非物质文化遗产7262 0 1 53!!!!!!!!!!!!!!!!!!!!!!!!!!!!!!!!!!!!!!!!"!!! "!!!!!!!!!!!!!!!!!!!!!!!!!!!!!!!!!!!!!!!!"!!! "勘误:本刊 2015年第 2期第 10页,第一段“21世纪 20年代”,应为“20世纪 20年代”。因编辑部工作疏忽,导致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为此诚挚地向读者致歉。①亚鲁王工作室,自 2010 年起在紫云麻山地区开展苗文音标文字教学。他能意识到这个东西价值很高,他说我,你把它搜集上来拿给我。记得我在我们村里边找了韦昌秀、陈老幺、陈老满、陈老四、吴老乔当年几个唱得好的。我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的,我跟他们说不怕,白天我让他们在我家里面,晚上偷偷地录。当时我在猴场镇粮管所有一小间房子,把这些人全部收拢来以后,请镇里广播室里面的罗兴义帮我们的忙,给我们提供设备录下来。我们录了整整三个晚上,把我们掌握的资料全部都录完了。我尝试做一些整理,但是汉文基础太差,最后也没有搞出什么来。我把收集的一整套送给我堂兄弟去了,结果他也没有成功,已经翻译了一部分,但是翻得不理想,他毕业以后就放弃这件事了,把带子也搞遗失了。虽然他是专门苗语系的,但也很难整理出来。现在亚鲁王工作室 ① 这些人,把它翻译出版,是很了不起的。我虽然对开路很有感情,但是受环境的制约,还是学得不够,不能说很全面。因为我们没有文字根据,日长年久一代传一代毕竟有漏的地方,是难免的。包括我自己,当时学的东西也有忘的,凭心去记记不了多少。以前开路有时三四天都唱不完的,现在慢慢地简化、省略,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也省略走了。如果像目前这样的话,要失传的。虽然国家已经重视了,但是大家的观念还没转变,需要造成一个气势,来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受限制的时间太长了,一下子观念转变过来很成问题。我小的时候办丧事来听的人非常多,过去房间都不大,全部挤满了人。老年人最多,年轻人其次,小孩子少。办丧事也是男女青年聚会见面的场合,所以有的人听得进,有的人听不进。凡是亲人一定要来,可听可不听,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注重了。我小时候听到别人唱就觉得很感兴趣,现在的小孩都听不懂了,也不喜欢听了。我们村里现在还不需要到外村去请东郎,还是够用的。年轻的东郎我们村伍姓的还有两个,韦姓的一个,我们陈姓的除了我还有三个,算是最多的。他们大部分还是不全面,能够掌握一部分。老的这一辈只有我算年轻一点,还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东郎,他们身体不好,都已经做不成了。这样算来,我们村总共有七个东郎。但是有些地方已经失传,像大田湾那一带,没办法只有请先生了。那边的苗族夹在汉族当中居住,就容易失传。有东郎的话还是要请,自家没有也要高价去请来,实在请不到东郎来给自家老人唱,就请道士、先生过来,心里面还是不平衡的。因为《亚鲁王》里面有我们的家谱,就像汉族的名字辈分一样的。在“文革”之前,每一个家族至少有几个青年人要自然而然去学习的。“文革”以后就很少了。几十年来我都是偷偷摸摸地搞,2008年我还是安排人放哨的,假如有其他人来我们就躲开了,现在能够公开做这件事情我真的挺高兴的。但是现在知道国家这样来重视的人是少数的,只有我们知道可以大胆地去做,下面的人还是不知道,还是很害怕的,比如在我们猴场镇还没有放开,假如你去谈到这方面他就避开话题了。我希望大 家 都 能 知道,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开路了(图 6)。图 6 置身人民大会堂的传承人陈兴华感慨良多(段新培/摄)西部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73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西部苗族史诗《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