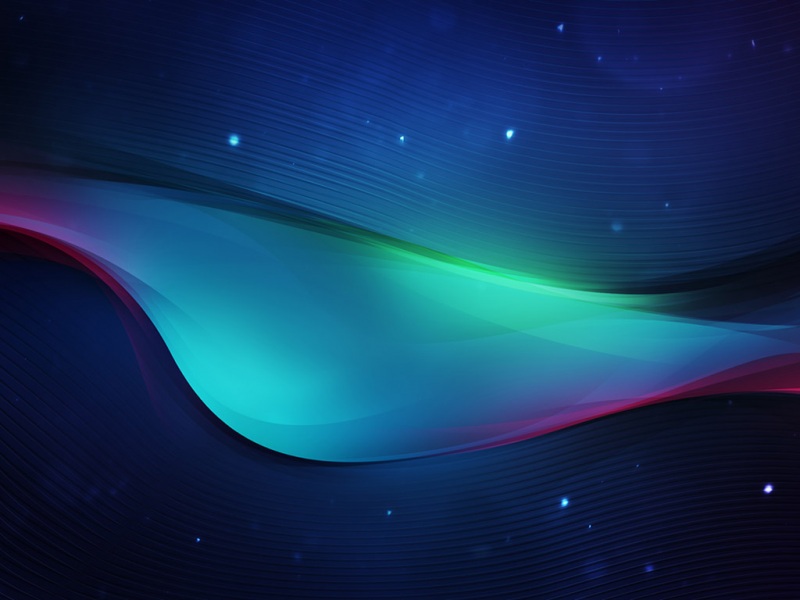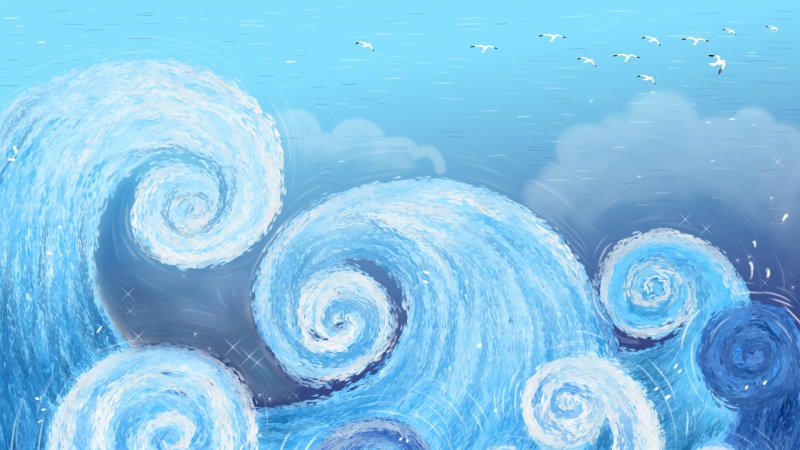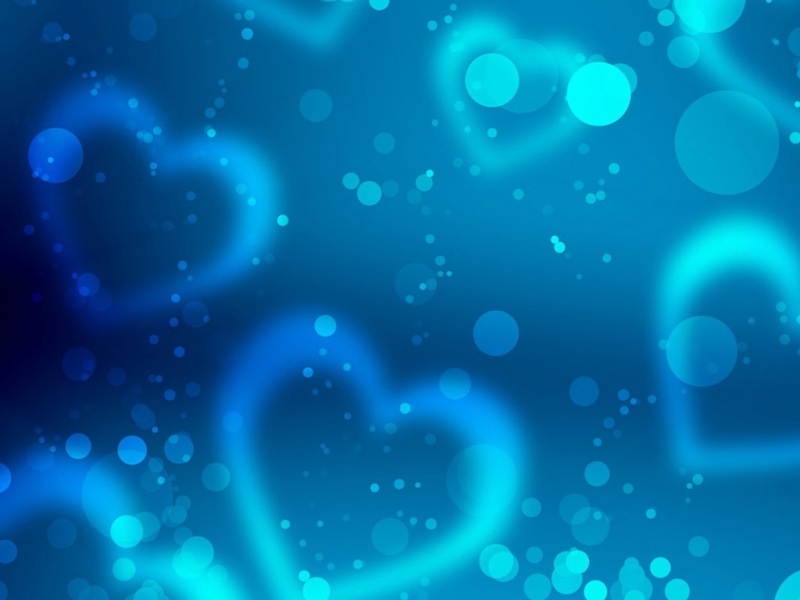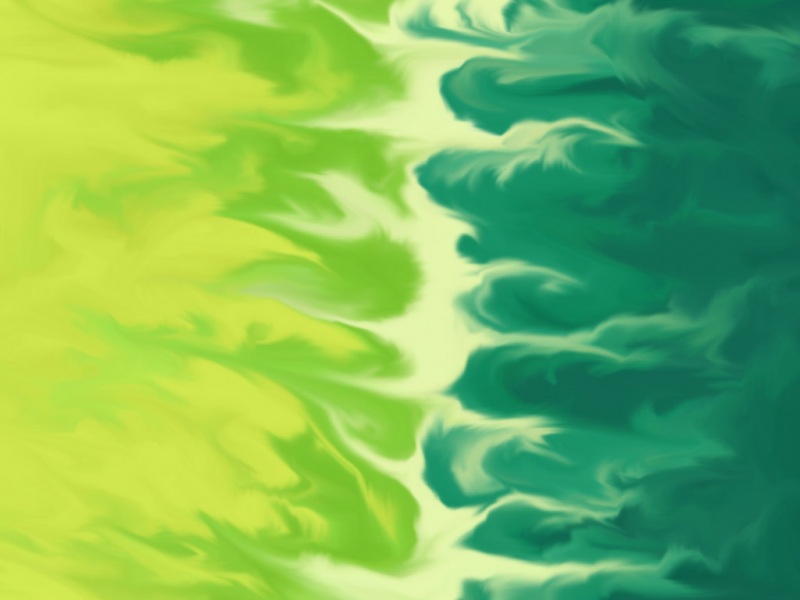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8570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8 分钟。
大饥荒年代轻灾区里的故事
山人
山人名符其实,老家在福建省鹫峰山脉深处。少时坐井观天,孤陋寡闻,据说大饥荒年代某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竟然闻所未闻!但是,其实在那大山深处,也摆脱不了大饥荒的阴影,也曾发生过许多让后人听起来宛若天方夜谭的故事。山人那时正处于小学生到中学生的转变时期,那些故事或为亲眼目睹,或为亲耳所闻。
(一)逃荒婚姻
由于贫困,加上历史上有溺杀女婴的陋习,老家曾经特别多光棍。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竟然有很多光棍娶上了老婆!——这是“乘人之危”,还是“救人一命”?山人至今还没弄清。但就凭这一点,我敢妄言自己家乡是全国的轻灾区。
我们县最早接纳逃荒女,是在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夏。那一年春节刚过,学校还没开学,小伙伴告诉我,去D叔家“看新娘”! D叔是我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四弟。当时年近三十岁,尚未娶妻。我们到了D叔家,果然见D叔带回一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跟我同龄,也属狗。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几年后才与D叔完婚),但四叔公已经让我们叫她“婶子”了。
没过多久,“婶子”的父母亲都来了,说是从浙江省龙游县逃荒来的,不逃走就会饿死。那一年,我的舅舅三十六岁,也还是王老五。“婶子”的母亲很热心,马上回浙江,把她的表妹带来,成了我的舅母。我的舅母那一年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开学后,我突然发现,小镇的街上多了许多陌生女人,她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都是从浙江逃荒来的。各村都有光棍娶上了浙江女。当时还处于“高级社”阶段,多数合作社对浙江女都挺关照,跟当地人一样分给口粮——那时农村还不大讲“户口”。二十多年后,我出差路过浙江金衢盆地,看着那望不到边的稻浪,真想不通:这么个米粮之仓,怎么会弄到百姓没饭吃的地步?
我们县接纳第二拨逃荒女,是在大跃进之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那年春夏之交的农忙假,我回生产队参加插秧劳动。集体所有的水田大都分布在一条通往闽东沿海的古“官道”旁。在汽车没有普及之前,古代的“官道”是山区的交通要道。沿海的盐巴鱼货等海产品通过古道流向山区,山区的茶叶笋干等山货通过古道流向沿海,全靠挑夫肩挑。古道用石块铺就,三里左右建一亭,三个亭的路程称为“一铺”(相当于十华里)。在这里劳作的几天,古道的凉亭成为我们午餐的临时餐厅,农忙季节的午餐一般都是送到田头吃的。
那些天,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群,从闽东方向往我们县流动,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不用说,那不是走亲戚,都是逃荒者。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见到凉亭的条板上坐着几位愁眉不展的女人,其中一人的怀里还躺着一个昏迷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约十来岁,面黄肌瘦。见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开饭,其中一位妇女开口了:“这小妹饿昏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给她喝点菜汤?”山里人大都心地善良,很快就有人将菜汤送到陌生女人手中,几勺子汤灌下去,那女孩就能张开眼睛了。这时,才有人开口问那几个女人从哪来到哪去。他们说从某县来,“那里有饭吃就到那去。”大家还都从自己碗中匀出一点饭菜,送给这几位逃荒女人充饥。午饭后,稍事休息。那个昏倒女孩的亲人开口了:“我这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我看到你们这里人心肠好,给她介绍个对象吧!”我真不敢相信:我猜十来岁的女孩竟然还大我一岁十六岁了?有人跟Z叔开玩笑说:“你十八岁,跟你最般配!”Z叔被说红了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Z叔的哥哥当真了:“找婆家?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那女孩的母亲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能给些饭吃就行。”
Z叔也是我的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三弟。Z叔当时还是我的同学,他上学比较晚,十七岁才考初中。不过在那时并不奇怪,每个班级都有些大龄学生——共产党执政初期比较重视“工农学文化”,许多在旧社会上不起学的,通过夜校等识字班学得文化知识,其中有些人还考上了中学。第二年,Z叔就辍学与那“拣来”的逃荒女结婚过日子了。我最近回老家曾打听Z叔的近况,说是他们的儿女在上海等地经商,他们夫妻也跟随子女到上海去了。
没过几天,C叔公也与逃荒女组成了家庭,并当上了“现成”的父亲。C叔公的父亲是我曾祖父的小弟,他和我们家的关系还没出五服。C叔公曾有五个兄弟,他排第五,两个哥哥与他先后被抓了壮丁。他在济南战役中当了“解放兵”,调转枪口参加淮海战役并一路打回福建,立过几次功,加入共产党,1955年复员回家,此时还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呢。他近四十岁了还没成亲,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五”。这回他走了桃花运,逃荒女送上了门,还给他带来一个五岁的男孩。别看我比那小孩大十岁,可我还得管叫他“叔”。这位“叔”在我老家生活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才回老家续他亲生父亲的香火。他的母亲又为C叔公生了一男一女。除了舅舅和C叔公,以上所有当事者都还在世,所以,请读者恕我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
因为都是女方送上门,逃荒婚姻家庭都还比较稳定,只有少数已婚妇女原配丈夫找上门私了或诉诸法院解决。我们县到底收留了多少来自闽东的逃荒女,我手头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可以肯定,由于闽东是近邻,闽东逃荒女肯定比浙西逃荒女多得多。我家所在那几个自然村(1961年后新建制为一个大队)人口才四百多。四百多人口的大队,收留的逃荒女及其带来的子女却达到二十多人,约增多了百分五的人口。
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年代,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穷县为什么还有能力收留逃荒女呢?是“天高皇帝远”,极左的风吹不到这里?还是这里的基层干部特别仁慈?还是左派朋友说的大跃进压根儿就没有饿死人那回事?笔者也曾经苦苦思索,想找出一些比较恰当的词汇加以回答。后来在共识网上看到高王凌的文章,称为“反行为”,或叫“猫腻”、“蔫拱”。我不禁为之拍案叫绝!
大饥荒之年不饿死人,主要靠“反行为”。山区农民很现实,也很机智。早在1960年就有人开始给所有地块估了产量。此后就是:风声紧,集体干;风声松,半单干;没人管,全单干。所谓“单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所谓“半单干”是指,水田集体耕作,旱地包产到户;或交通要道旁土地集体耕作,偏僻地块包产到户。在我1969年正式回乡之前,其实每年春节期间也都要帮助生产队“算账”——年终分红。不管集体干,还是“单干”、“半单干”,多数生产队都备有两本账:一本应付上头检查,另一本才是真账。丰收之年少报点产量(即“瞒产”),也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具有优越性?从山区农村看,根本不具优越性。
(二)“偷猪案”
我家相邻的一个公社,曾经发生过轰动全县的“偷猪案”。案件据说牵连到几个大队的近百号人。后来在文革中,我从揭批那个公社书记的大字报中看到,这个“大案、窝案”其实并不复杂,甚至于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了,其实只不过是老百姓“饥不择食”罢了!
1958年秋天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宣称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其中“牧”就是发展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农民都到大食堂吃饭,各家各户自然养不成猪了,各大队和公社都办起了相当规模的养猪场。
那年秋冬天,养猪场的猪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上“共产主义天堂”的生活。据说粮食多得吃不完了,与其让番薯烂在地里,不如让养猪场拉去喂猪。还有,大食堂24小时开放,“放开肚皮吃饱饭”,那剩饭剩菜、米汤泔水、米糠麦麸源源不断地送往养猪场。那些猪一头头都吃得肚圆臀肥!
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春节过后,粮食开始吃紧,食堂开始定量供应。人都吃不饱饭,还有粮食喂猪么?可怜的猪们,只好委屈你们吃青草了!像水浮莲、马齿苋、鱼腥草和浮萍等,都是可作猪饲料的“猪草”。农民一家一户养猪的时候,母猪、子猪要吃精饲料,而喂到半大的肉猪“豚”,就可喂粗饲料——猪草煮米汤泔水拌米糠麦麸。不巧,此时“水肿病”开始蔓延。据说治疗这种病最有效的,就是吃米糠。本来用于喂猪的米糠,现在被加工成糠饼,成了治病救人的药!那些猪一头头瘦得像老鼠!接着,猪也开始出现“营养性死亡”(对不起,这里借用孙经先先生的词一用)。死猪越来越多,个别饲养员白天按场领导的命令上山埋死猪,夜里就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把猪尸体挖出来,一起“分享”死猪肉。据说,还有些猪并未断气,也被用这种方法给分食了。许多集体养猪场其实都发生过这种“偷猪”现象,只不过一时还没引起领导的关注而已。
庐山会议整肃了彭德怀之后,不知为什么毛主席突然对养猪来了雅兴。1959年10月31日,他在批阅河北等地养猪报告时,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要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毛甚至把养不养猪,党委重视不重视养猪上纲上线到“世界观”问题:“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
来了最高指示,各级党委还敢怠慢?某公社书记立马开始视察养猪场。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养猪场几乎无猪可养了!
再说,那些分食“死猪肉”的事,也不可能密不透风,还是有人把他们告发了。公社书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的典型要案,上报给县委。县委责成公安局破案。公安局派了一名副局长坐镇。那时破案讲究“群众办案”:召开群众大会,让被检举人上台一一坦白交代。如不交代,就让民兵“帮助”他们——双手反绑,吊到梁上,我家乡称其为“老鸦吊”,也就是后来文革中常见的“喷气式”。被检举人被吊得难受了,只好交代: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偷宰死猪(病猪),分给谁谁。只要一个人嘴被撬开,就会牵出一大群。就这样,“偷猪案”告破,重者被判刑劳改(一般都是吃过死猪肉的“黑五类”及其子弟),还有的被判“管制劳动”,有的被罚做“苦工”,牵联近百人。我的一位同学的继父被吊打后,落得双手终身残废。
近年来,有人歌颂毛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大跃进”之后那几年,“夜不闭户”是真——包括门栓在内的所有铁制品全都搜去“炼铁”了,“户”闭不了啦!“路不拾遗”可不见得,小偷特别多。偷什么?偷吃的,除了上面说的偷“死猪”,更多是偷地瓜、南瓜、青菜之类。水稻熟了,还没开镰收割,外沿一圈穗子被人偷剪的事也常发生。
(三)远房叔祖之死
远房叔祖叫清黎,已出五服,其实只是同在一个祠堂祭祖的本家而已。我爷爷的爷爷也是“清”字辈,所以称其“叔祖”,方言称“大公”。
我上小学时,每天清晨从自然村出发,临近小集镇的路口,几乎都会遇到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老汉,提着粪筐拾猪粪。一回生,二回熟,多见面了就成了“朋友”。清黎老汉特慈祥,我们都亲切地喊他“大公”。
清黎老汉每天拾完猪粪回家,吃了早餐,就送一大群母鸭下田。有时,我们放学晚了,在路上也正好与他照面——他正赶着一大群母鸭回家。1958年秋天,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我们这些高年级小学生也停课参加挑砖挑炭,“人小志气大,敢叫土高炉开花”。而清黎老汉也不再拾粪和放鸭了。
公社化以后,清黎老汉的鸭子全都宰杀了,“营部”(当时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公社称为团部,大队部称为营部)分配他的工作是放牛。放牛与放鸭,差别仅在地点:一个上山,一个下田。那一阵子,青壮年劳力都炼钢铁去了,收割水稻和加工地瓜米(将番薯切成丝状,晒干)的活都由老人和妇女干,眼看许多稻谷和番薯都烂在地里,他觉得心疼。牛群回栏后,他还会主动地帮忙干些活。那时,天天晚上点着松明火把“出夜工”,整个小镇只有一个大食堂,且实行“放开肚皮吃饱饭”,几乎24小时都能吃到饭。老汉饭量大,干的活也多,手脚一辈子都闲不住。
1959年春夏之间,我听说清黎老汉死了。那年村子里特别多老人故去,死前多得过“水肿病”。关于清黎老汉的死,除了“水肿病”,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情节。1959年春天,每餐只能领到一小碗饭。清黎老汉在山上放牛,经常饿得眼睛冒金星。用指头轻轻按双脚掌面,就能看到深陷的指痕——那就叫“水肿病”。双腿越来越不听使唤,经常撵不上牛群。那一天,他赶着牛群来到一处山谷,老牛小牛都显得出奇的温驯。他上前一看,喜从天降——满山谷都是刚刚长出的甜笋!原来,牛们遇上盛宴了。
甜笋,我老家叫“发笋”,是一种野生竹子长的笋,味道是甜的,把壳剥掉就可以生吃。“发竹”叶子酷似大熊猫爱吃的箭竹,只是杆比箭竹粗多了,可作晾衣的竹杆。“发竹”常与其他树木混生在一块,繁殖并不特别快。一旦其他树木被伐,它们就可能猛长出幼笋,这大概是被称为“发笋”的缘故吧。“全民大炼钢铁”把山上的大树都砍倒烧炭,凡是大树伐倒的周围,甜笋都特别“发”。清黎老汉正饥肠辘辘,眼睛一亮,一边猛采,一边猛吃。一个上午下来,他也记不清吃了多少。最后挺着大肚子,赶着一群肠满肚圆的牛群回家。那天晚上,他就吃不下晚饭了。躺到床上,开始腹胀、腹痛。儿子连夜请来公社卫生院医生,医生说是消化不良,开了点药就走了。老汉腹部鼓得老高,滴水不进,过两天就呜呼哀哉了。
清黎老汉之死,有人说是“撑死”——确是被甜笋撑死呀!有人说是“饿死”——不是饥,岂能不择食而撑死?有人说应属“寿终正寝”——六十多岁老人,已经到“天年”了。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有谁能为他认定?个案不能认定,又何来全县、全省、全国的非正常死亡(饿死)统计数据?
(四) “套饭吃”、“苏打饭”和“校园篝火”
1960年9月,我被录取到县城一中上初中。新生报到时就被告知:学生必须向学校购买统一规格的陶制炖罐,做上自己记号(例如写上学号),向食堂交了饭票,按所在班级,放置在固定层号的蒸茏里,由食堂统一放粮食和水,然后开蒸。未到开饭时间,不得进入餐厅,必须排队在门口等候。听到值日教师口哨声,餐厅才开门。学生鱼贯而入餐厅,先找自己班级的蒸茏,然后找到自己的陶罐。回到自己的餐桌旁站立着(不配凳子),等候值日教师吹口哨并喊“开动!”才开始狼吞虎咽……
这么严格的“就餐纪律”,名义上还是1958年号召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实质是为了防止学校出现“就餐秩序混乱”。那年代几乎没有食油供应,更谈不上肉蛋等副食品。正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中学生食量都特别大。每餐吃三四两(指小两,1斤合16两)连半饱都没达到。上午第四节课饥肠辘辘,其实都无心听课。
食堂墙上贴着关于“偷饭吃”和“套饭吃”的处分办法。“偷饭吃”好理解,就是甲偷吃了乙的饭。在那年代,乙就只能饿半天肚子。街上饭店吃饭要交粮票,有粮票也难找到饭吃。所以,“偷饭吃”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可耻行为,处分这种行为的学生,大家都没意见。
另有一种行为其实是利己不损人的:星期天偷偷跑回家吃饭,或者到亲戚朋友家“蹭饭吃”,或者到野外找点食物“野餐”。这样一来,就有剩余的饭票,找一个备用炖罐,就可多蒸一罐饭,吃“双份”。我们中学总务主任挖空心思,把这种行为称为“套饭吃”——属于“扰乱就餐秩序的违纪行为”。偶尔发现一次,给予批评,扣所在班级评比分。多次不改,也要受纪律处分。于是,值日老师会到餐桌上巡查,是否一人一罐饭;在餐厅出口巡查,是否有人把罐饭带出。如有这些现象,就要盘查(给生病同学带饭,要说出房号,等等)。
这种反“套饭吃”,学校大约坚持实行了两年多。其间,一些男生家长反对声颇高。学校也是采取过灵活措施,如允许学生在自己的炖罐中加放些食物,如地瓜、豆类、花生、马铃薯等。后来,学校干脆让学生自己保管粮食,吃多吃少由学生自己安排。“套饭吃”一词终成历史。
学生有了“吃饭自主权”,有利也有弊。毕竟口粮太少,月初吃过头了,月底就要过紧日子。有同学发明了“苏打饭”,并在学校风行过一阵子。“苏打”,学名碳酸氢钠,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发泡剂。“苏打饭”,就是在米淘好后,放入少量苏打,同样量的大米,会多蒸出几成的米饭来。从视觉上看,“饭量”多了,吃下肚子后,反而更早饿肚子——苏打提高了胃肠的消化能力!
不知哪位同学带的头,晚自习下课后在山坡上点起了漫山“篝火”。那“校园篝火”不是青少年“队日活动”、“团日活动”之火,也不像现在青年人“烧烤”之火,而是“充饥之火”。充饥野炊的几要素如下:
灶:从古书上“埋锅做灶”得到灵感。我们学校在山顶上,那时山坡上树木稀少,而且已经被师生开垦成旱梯田。选个避风的田埂,向下挖个洞,洞壁朝外开个灶口、朝里留个烟道便成。
锅:学校附近有个制陶厂,花5分钱就可买到一个正品陶罐,次品只需2、3分。不花钱也可拣到废品——烧制时变了型或磕碰出缺口的陶罐。当然,重要的是,陶罐的口径要与“灶”相适应。
柴:从建校开始到我们上学时,从未停止过“愚公移山”,山头不断地被削掉,开辟成操场,或供建校舍。挖山的时候,会挖出大大小小的树根,周边农民拣走大的当柴烧。小树根没人要,经过多年雨淋日晒,已经干透,十分好烧。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年代,学校食堂烧的柴,相当部分是学生上山砍的。上山砍柴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带些“自留柴”。所以,柴火不成问题。
灶、锅、柴都有了,再有食物就可“野炊”了。“野炊”的食物主要来源有:
第一,从家里带来。第二,自己的“小自由”地里种出来的。那时农村,与“大集体”相对应的农民自己开荒种菜的地,称为“小自由”。我们学校师生们也在山坡上开垦了许多“小自由”,种下蔬菜、番薯和马铃薯。我记得自己开垦的那片“小自由”梯田,紧挨着男生小便池,“近水楼台先得月”,施肥较多,种的葫芦瓜和马铃薯都获得大丰收。葫芦瓜每只都有两三斤重,一个陶罐当然煮不完,就分给同学各自去煮。第三,拣来。有得拣?有。星期天扛一把锄头到农民刚刚收过番薯的地里,胡乱地刨,经常会刨出农民遗落在地里的番薯。有时,半天能收获一二十斤。上山砍柴可能会遇到野笋(“发笋”),顺手采一些并不难。有些同学星期天还下田下河摸鱼虾贝类,也会有收获。最差的,就是到番薯地里拣些“地瓜叶”,煮熟了放点盐,也可充饥。
在我记忆中,初中寄宿男生几乎没有不参与“野炊”的。每天晚上下自修以后,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埋锅做灶”。从街道往山上看,真是“点点篝火”呀!尤其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蔚为壮观。这种现象持续了好久。1961下半年,随着大量学生的辍学而暗淡,1962年底随着粮食形势的全面好转而完全熄灭。我们60级初中,入学时四个班220人,初中毕业时只剩两个班,总共不到60人。辍学率高达70%以上!饭都吃不饱,还有心求学么?
(五) 大程与小程
七十年代,山人跟随工程队到福安县施工。福安畲族民工力气很大,饭量也很大,一餐能吃下一斤大米煮的干饭。他们自己也经常议论:胃肠都是在“困难时期”撑大的,那时没饭吃,地瓜叶、树叶、树皮、树根都吃过,吃着吃着,肚皮就大了。所谓“困难时期”,就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年代,当时才过去十年,记忆犹新。我问:真的有人饿死么?他们说:怎么会没有呢?惨了,村子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有时一天抬出好几部棺材呢!我问:这样的饿死人持续多久?他们说:记不清了,反正不会很久。听说叶飞(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派人来调查,撤了县委书记的职,政府送来救济粮,后来就没再饿死人了。
这时,一位曾在地委机关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确有其事。叶飞过去是闽东苏区的的创建人,老区有人写信告到他那里去了,他还能不派人来调查?地委书记程少康一听到风声,就急忙找福安县委书记程广英:“小程呀,我姓程,你也姓程。你小程倒了我大程如果不倒,你还有翻身的机会;你小程倒了我大程也倒,你可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程广英果然是明白人,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受到撤职的处分。可没过多久,真的又当上县委书记了!
这位同事说得绘声绘色,好象他就在程少康身边似的。我说:“大程小程的谈话怎么被您偷听了?”他笑着说:“从地委大院大字报上看到的。”
“丢卒保车”本来就是一种策略,但大字报上的故事,我们不能信以为真呀!
同事说:那倒也是。但同样一个福建省,其他地区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闽西闽东出现了,地委书记当然有责任。同样一个福安专区,其他县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福安宁德两县出现了,县委书记怎么没有责任?
我说:大程小程固然有责任,叶飞难道没责任?我认为,和平时期,省里出现成批人饿死,省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侃叶飞的时候,他还戴着“福建第一号走资派”的帽子。后来才知道,叶飞在当时的“诸侯”中不算太左,所以,福建在大饥荒年代不算重灾区。
同事说:叶飞有责任,他上头难道没责任?我看,上头要担当主要责任。
我说:是的,毛主席说过: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你看,叶飞的上面还有谁?不就是刘邓吗?——我当时收藏有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为《党内通讯》写的一篇文章。这些话都是那篇文章里说的。那时,我特别欣赏这篇文章,不但内容说到农民心坎上,而且文笔也特别好。
同事不以为然地一笑,轻轻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他不赞成我说的话,但又不便再说明。直到文革结束、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才逐渐认识到:1958年秋天狂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主要责任不在“大程和小程”们,也不在“叶飞”们,而在毛泽东!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大饥荒年代轻灾区里的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