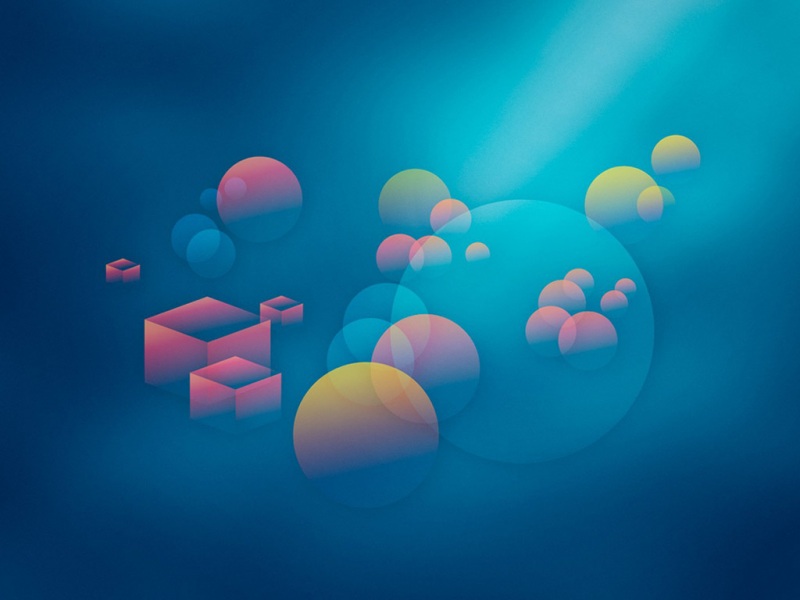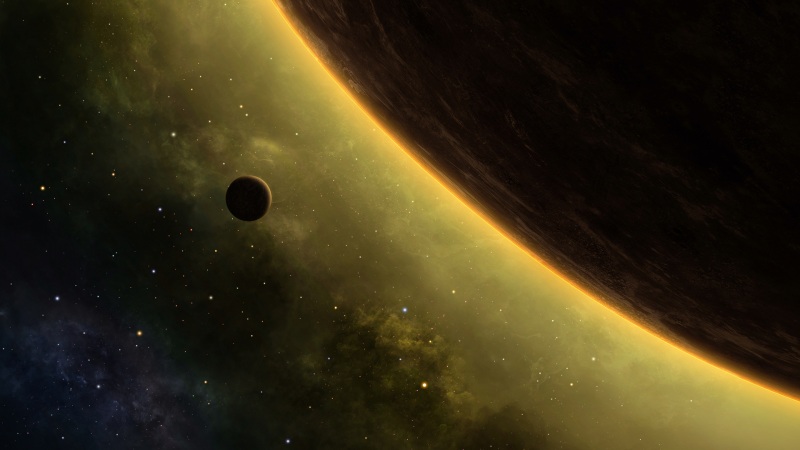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3518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8 分钟。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成功,并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山野里的爱情故事,而是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山野里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含混的故事,它以爱情的惨败收场,而这爱情的惨败却正是浪漫主义凯旋的号角,当这号角响起时,你却听见的是现实的声音。
目 录1. 搞错地点的人们
2. 故事发生在哪儿?
3. 关于凤凰山
4. 铜山与“金山”
5. 小提琴与闹钟
6. 老磨工的下酒秘法
7. 不死的浪漫主义
8. “鸟”的谜语
9. 四眼母子的生存哲学
10. 基督山伯爵的意象
11. 90年代末的天池
12. 谁是“小裁缝”?
13. 山野里的爱与美
14. 垄断爱的解释
15. 千禧年的落幕
作为对角色原型有些许耳闻的旁观者,作为在电影所描绘的地方生长的体验者,我很难对这部电影做出客观评价。无论我怎样尝试,这些场景和演员总是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家乡的旧房子、山林里的水塘、有好有坏的乡里乡亲、小镇近30年的是是非非,以及那位曾在某个夏天来家里帮工的裁缝阿姨。在县城的传闻里,她就是“小裁缝”的原型。
原著小说出版后,作者戴思杰有回到过县城。当时,县城里的人们普遍不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就像故事里那些听知青讲电影的乡民们——他们认为小说、电影都是真实的,于是,县城里就有了很多关于这位裁缝阿姨的传言。戴导在这期间曾与县城宣传部的相关领导有过会面,据说,他在当时澄清过,“小裁缝的角色不是特指某人,而是艺术符号的集合。”我不知道这种澄清是否有用,我也不认为有向当事人追究事情原型的必要。那样太不礼貌了,既不尊重当事人,也不尊重文艺作品的创作价值。
导演戴思杰搞错地点的人啊无数的影片简介、影评都犯了严重的地理错误,说故事是发生在湘西,让我怀疑这些信口胡说的人根本没仔细看过电影。
这让我很是恼火,一方面,莫名的地理置换无端在冒犯我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这更是对电影及其创作者的冒犯。电影里已经有很多线索指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至少能精确到县级。犯了地理错误的人,要么没看电影,要么是个傻子,要么是个不看电影的傻子。当然,无论是哪种人,都满足成为大众影评人的标准,尤其在豆瓣。
很明显,故事不是发生在湘西的。如果有一部电影,乡民台词都用的是东北话,你们能相信它是描绘发生的西安的故事吗?那么,这部全程用四川话拍成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又怎能成为一些人所说的发生在“湘西”的故事?虽然电影是在张家界取的景,那导演煞有介事地让所有人都讲四川话又是何种用意?就因为电影里有凤凰山,就肯定是讲的湘西凤凰山?那贵州省境内的一大堆凤凰山作不作数?
当然,故事的发生地也不是在三峡附近。有人紧紧抓住电影结尾寻访小裁缝部分关于三峡水库移民的对话,却忽略掉了之前的所有线索。然而,事实是,原版法文小说《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是没有这部分的。我不知道导演在电影里加上这段是何种用意,或许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虽然最后还是没过审),比起原著,电影已经删减太多细节了,又或许是导演心里有些话在小说里还没说完,需要一个这样的补充,这似乎也是他后来回访县城的初衷。我不清楚戴导回国的确切时间,因此,也不必对他做太多揣测。总之,在电影里,导演已经不顾上这段戏与先前有地理位置上的出入了。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豆瓣简介故事发生在哪儿?电影开篇,刘烨饰演的马剑铃在第一段台词里就说了,他和罗明从天全县走路两天才到达凤凰山。此后,“天全县”三个字又在诸多台词里反复出现,除了作为道具的单位挂牌写了“天全县……”(连写法也给出来了),甚至在寻访小裁缝的戏份里,村民也说了“天全那边的人也要来”。至此,我烦请各位打开手机、电脑,搜一搜“天全县”三个字,看看它究竟在哪里。我想,能在这么明确的指示下仍把故事发生地搞错的人,是理应受到刻薄言辞的苛责。
从第一段台词可知,故事发生在四川省境内一个与天全县相隔两天路程的小村庄。很快,在电影算上片头都还不足10分钟时候,刘烨的旁白又给出了第二条线索。他说,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同性恋皇帝把这座山赏给了他的男宠开矿铸币。现在,我们打开搜索框,输入“汉朝 同性恋 皇帝 男宠 铸币”,立马就可以在搜索结果里读到汉文帝和邓通的故事。据《史记》记载,邓通因受汉文帝宠幸而得了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获得了铸币权,因而成了一方巨富。在此,我们又可以查到,蜀郡严道县,就是现今的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
无论如何,仅仅从电影开篇,我们是能够把故事发生的地点确定到县一级的。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曾在山顶上看过雪,在天池边玩耍过,听过县城里的传言,你也会确信这是发生在天凤乡的故事。或者,当你打开一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译本《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小说会告诉你确切地址的。
表面有特殊凸起的“邓通钱”关于凤凰山电影里说,凤凰山(原著小说里的天凤山),就是铸币的铜山。或许是时代有变,地理名称有变,或许是戴导的艺术加工,在我记忆里,只有天凤乡,没有天凤山。文献里的铜山,就是现在的宝子山,山峦北边有一座天池,再往北走,就到了天凤乡,要是再往北些,就出了荥经县界,到了天全县。为了记述方便,无论是现实里的宝子山,还是作品里的凤凰山或者天凤山,我都统一把它称作铜山吧。
电影开头提到过一位米歇尔神父,并引用神父的记载,讲出了汉文帝和邓通的故事,只是,略过了小说里提及的“鸦片种植”。小说里写到,这些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村民,很可能以前就是种鸦片的。没错,有这个可能。民国时期,四川、西康(含今康定、雅安、马尔康地区)都是贩烟大省。《让子弹飞》改编的原著《盗官记》讲的也是这段时期的事。我曾听县城里的老人讲过,当年,似乎是刘湘军队还来抢过鸦片,被县里的“袍哥会“(四川地方武装组织)打跑了。后来,当地的袍哥会又在解放西康时出了力,并借此入了编制,不过,在接踵而来的的三反五反、三年饥荒、十年文里革,熬到寿终正寝的袍哥似乎不多见。按照电影里的时间计算,如果村长在1971年是60岁,那么,在鸦片黄金期,他确实正是合用的青壮劳动力了。
在电影里,铜山是天全县的辖区。我不知道是艺术处理还是这几十年来周边县界有更改。按理说,作为凤凰山原型的铜山从一开始就隶属蜀郡严道县,在10多年前,严道镇也仍旧是荥经县城的中心,这么说来,铜山是没有划归天全的可能。但我记得,在90年代末,确实又重新划过县界。当时,荥经、洪雅两县为了另一处可做旅游景点的瓦屋山争得不可开交。在当地小学生的传闻里,为了这场争斗,双方还出动了各自的黑社会势力,相约在瓦屋山脚下进行了一场对决。最终,荥经的地痞流氓不够洪雅凶狠,便输掉了瓦屋山。对此,我不知真假,这或许就是那几年《古惑仔》文化的影响吧。
《让子弹飞》剧照铜山与“金山”
我很少回故乡了,现在想起,也不清楚荥经县还有多少人知道“铜山”的出处。但我确实记得,似乎是在90年代,县里有修建过一座贴满了绿色玻璃的“铜山大厦”。在那些年的县城文艺界,还活跃着一位笔名为“铜山耕夫”的知识分子前辈,县城的很多地方也都留有他的笔墨。
说起来,这座铜山大厦应该是靠着县城另几处“金山”修起来的。虽说是“金山”,其实一点也不产金子,产的是硬度极高的石头——花岗岩。90年代初,县城里的人靠着花岗岩满满地捞了一笔。通常是这样的情形,三五个好友借钱合伙,去矿山上拉一车矿石,再租用一阵切割机、磨机,雇几个工人切割、打磨成俗称“毛板”或“精板”,最后雇一台货车,跑上一天一夜,拉到成都建材市场找买主。这一趟跑下来,刨除成本后,每人能分得的利润差不多抵得上三年的工资。
在这段满地捡钱的日子里,再没有人愿意好好上班了,况且,县城单位总是没太多事可做的。有些人胆子大,能空手套白狼;还有的人胆小些,但稍微精明些,也能靠借贷把资金链盘活;剩下的老实人,只得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财。在这段时间里,县城总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连街头的无名服装店也能把普通的polo衫卖到300块,很多工薪家庭的小孩也有机会去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学习。在我小学的时候,50人的班级里,连我在内就有3人在学习小提琴,除了我,另两位后来都去了川音附中,直到念完川音本科、研究生。
小提琴与闹钟
当电影里的马剑铃拉响小提琴时,我总会想起我的小提琴老师。他的年纪和戴导差不多,似乎是在“上山下乡”活动时听过哪位知青的演奏,由此便喜欢上了小提琴。我从未打探过老师的师承,但我可以确信,他不是荥经人,因此,他听到的琴声,不会是来自戴导或他的哪位朋友。而且,他们所处的年代也对不上。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更多是对苏联农场模式的效仿,和后来文革时期的“插队”不同。
马剑铃是幸运的,靠着罗明一句“莫扎特想念毛主席”的鬼扯蒙混过关,能在这穷乡僻壤享受演奏《莫扎特奏鸣曲》的乐趣。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虽不算稀奇,但也要碰运气。文革时,文学家、艺术家、翻译家,要么去死,要么洒脱地作践自己、作践艺术,以此谋求一条活路。我的老师不如马剑铃幸运,没有蒙混过去。在十年文革里,他少有碰琴的机会,更多时候只是躲在被子里偷听奥依斯特拉赫的录音。
当然,无论是哪个年代的知青,无论他们是作为“援助者”或是“再受教育者”,他们的身份、知识背景都早已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记。他们仍是不同于普通的乡野山民,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之外,他们的学识和艺术素养总会吸引村民的耳目。至少,他们的出现,让一些未受教化的人们产生了对知识和艺术的原始向往。哪怕知识不一定能改变人的命运,对知识的追求至少让人可以去追寻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的老师抓住了这个机会,电影里的“小裁缝”在追逐这样的机会。
那些年里,老师每周都在雅安各个区县奔波,每个地方只待上一两天。回想起来,当我们这些学生和学生家长盘算着他回到县城的日子,心情就像电影里等待着罗明讲电影的乡民们一样,等待着他带来关于外面世界的新消息。
就像马剑铃的闹钟改变了村里的作息一般,老师也为县城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是闹钟还是小提琴,都成了一种符号,这些被崎岖山路困在原地的人们,通过它们试图与外界产生些联系。人们每日照常过活,而又总要隔山差五地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似乎是在提醒外界,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
拉小提琴的马剑铃老磨工的下酒秘法
老磨工所在的千丈崖,原型或许是天凤乡附近的天棚山。只是看看这样的名字,便明白了它的艰险、陡峭。是什么样的人会住在那样的地方?只有老磨工这样的人,邋遢、懒惰、散漫。小说里对老磨工的描绘比电影详细了很多,他嗜酒,住在满是虱子的棚里,常拿泡过盐水的石子含在嘴里当下酒菜,酒后会唱些“淫秽”的山歌。
石子泡盐水的法子绝对不是杜撰。不只在荥经山区,在重庆码头地区,一些老头也有这个习惯。可见,这个穷苦的解馋方法,在巴蜀穷人的亚文化圈里是有广泛流传的。据我猜测,这可能是晚晴闹盐荒时候传下来的秘法。很多人都不了解近代四川闹盐荒的事。这是对当代四川民风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甚至影响了现代川菜的成型。
常有人说,川人嗜辣,是因为四川盆地湿气重,要多吃辛辣食物除湿。都他妈是放屁!看看闽粤,湿气都已成了瘴毒,照样坚持不吃辣椒。况且,从有据可考的地方志看来,近代以前,四川人是不吃辣的。唐宋时,四川是蔗糖大省,川人嗜甜,来历不明的“东坡肘子”便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明末清初,四川是盐产地,川人嗜咸,此时,辣椒是作为观赏植物而受士大夫喜爱,看它红绿相间,讨人喜欢。到清朝中后期,食盐在官营体制下已经溢价了八九倍,再遇上南北漕运的水路被太平天国截断,朝廷只得强征四川产出的食盐调往京师。至此,川人再吃不上盐了,只得学苗人用辣椒调味佐餐。是的,你们没看错,最嗜辣的其实是贵州苗人,因为穷,没多少调味料能吃。
从好些年前开始,如果你乘坐川航的航班来成都,到了就餐时间,就会看到有空姐拿着一罐“老干妈”辣椒酱,满场问人“要不要加辣椒?”这就是现代四川的境况,到底是文化如何贫瘠的地区才会拿着一罐来自外省的特产彰显自己无明且狭隘的文化地域主义情结呢?有机会的话,请千万记得告诉他们,“老干妈”,其实是贵州特产。
贵州特产“老干妈”不死的浪漫主义
老磨工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穷得一塌糊涂,连无产阶级都要嫌他穷。在我看来,他却是这群人里最具小资情调的人,也从来不和“劳动人民”这样的词沾边。
经过许多年的语言大清洗,“劳动人民”已经成了自动包含如勤劳、勇敢、坚毅等许多特质的词组。这个穷鬼,真切地把自己活成了这些词汇的反面。他是一个比很多资产阶级更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活脱脱就是生活的艺术家。在他的生活里,除了音乐和酒,千事万事可都去他妈的吧。
如果有人告诉老磨工,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的反应不过是一句“啥子浪漫哦?”这是他在电影里对“浪漫”的回答。对此,戴导借马剑铃之口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真诚的、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
以我看来,这是中国化的“浪漫”概念,缺少了原词“罗马式”的激情。不过,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解释看作一种概括。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体验(情绪的、感官的),这些是无法被掩盖的真实,因而是真诚的。它是真实的、个体的,因此是反威权的、不可操弄的,它具备的独一性、真实性、存在性共同构成了它的美学价值,因而,可以说它是“美好的”。
很多关于《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电影、小说的简介都说,这是一个山野里的浪漫爱情故事,似乎默认了“山野”和“浪漫”总是捆绑出现的美好事物。不,不是这样。在很多乡野地区,就像在电影里的天凤乡一样,“浪漫”是一种稀缺物。在这里,《莫扎特奏鸣曲》必须假以“莫扎特怀念毛主席”之名才能够被演奏、被聆听。人们看重“名义”甚于“本质”太多,用“名义”划分人群、书籍、艺术,制造了太多的隔阂,而忽视了同为人类所共同经受的欲望、诱惑。看看这群同是被时代摒弃的人们吧,他们甚至拒绝相互的慰藉。
在这一个的环境里,无论是罗明对小裁缝的爱慕,还是马剑铃听老磨工唱的山歌,都是在追求稀缺的浪漫主义。如果把小裁缝看成萌芽阶段的浪漫,那么,老磨工便是浪漫主义的终章。
这个老头,又穷又惨,可他不在乎,管他妈呢。在他的山歌里,爱情更忠实于欲望,是满怀着元初混沌之力的浪漫。这种张狂的激情弥补了中国化“浪漫”的不足,为这躯体降下了罗马的灵魂。
他若是幸运些,哪怕只是出生在东欧,或许有机会成为山野里异军突起的摇滚乐手,在布拉格广场上竭力地用他的琴声和歌声与苏联的枪炮对抗。若是他倒霉些,出生在柬埔寨,很快便会因摇滚乐手的身份被砍头,被丢弃在历史的积满灰尘的档案袋里,直到未来哪位白人游客打开这破旧的档案袋,找到他这首备注为“What a bird!?”的传世名作。
“鸟”的谜语
因电影不同于小说的表现手法,戴导在这一段没有使用小说里的“虱子歌”,而是另外选用了“鸟之歌”。让我们来看看这段浪漫至极的淫词吧。在这一部分,我将选用更原始的用词,对电影给出的台词做些修改,希望各位不要在字词上过多纠缠。如下:
啥鸟飞来节节高?
啥鸟飞来像双刀?
啥鸟飞到天池里?
啥鸟飞来伏青草?
鹞子飞来节节高;
燕子飞来像双刀;
雁鹅飞到天池里;
野鸡飞来伏青草。
这是一段极好的电影改编。伴随着老头的歌声、三弦声,画面切到了罗明和小裁缝在天池里嬉戏、做爱的场景。歌声末了,处男马剑铃当然猜不出这是什么谜语。谜底是什么,我想,这段画面剪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看到很多人对此歌谣的意思有过争论。有人认为,歌谣已经讲明白了,鹞子、燕子、雁鹅、野鸡就是答案,不存在谜底。有人认为,“鸟”“天池”“青草”是对男女私处的隐晦描写,而“双刀”指的则是男女交合的场景。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前者强调歌谣本身,后者强调歌谣的起源及艺术改编。接下来,我将理清两者的区分。
首先,这不是四川山歌的改编。根据现有资料表明,这原是江南地区的山歌。精确一点的话,可以追溯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镇(现已并入川沙新镇)。根据《浦东史志·六灶镇志》可知,这是《答还山歌》的一段,原曲是用问答的形式唱出来的。在电影里,原曲的“太湖梢”换成了“天池里”,让它成了更有地域特色的山歌。
这种山歌形式在各种地区文化里都很常见,常常是被归为儿歌的形式,因为,儿童可以在这问答游戏里学到很多日常事物的名称。便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样的歌谣有何“淫秽”的含义。确实也有一些江浙人说过,这是他们记忆里的儿歌。我想,正是因此,一些观众便认为,谜底并不存在。
可惜,这些观众抓住了歌谣本身,却忽视了电影。也就是说,当一些元素出现在电影里,它们便不再是生活里的“本身”,它们是为电影表达技艺而服务的工具。当歌谣作为工具时,它与这段剪辑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个“谜语”。基于电影艺术,谜底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从山歌艺术的创作手法来看,这首歌谣最初很可能就是男女调情的山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答还山歌》完整版,山歌问答前半段围绕“哥哥”与“小姑娘”的特征不同进行区分,事物特征多围绕“长”“短”“贵”“ 糨”展开,在后半段里,又多围绕“鸟”“花”来提问,并有“结子”“叫声”等讨论。从大多数问答山歌的创作流程看来,原始的山歌可能就是“男方隐晦地表达求偶意愿却被机灵的女方见招拆招”的故事。随着对歌习俗的遗失,山歌的隐晦含义也逐渐被淡忘,经过一些词句的修改调整,便成了小儿生活知识启蒙的儿歌。
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明朝文人冯梦龙在吴越地区采编的《山歌》集子收录了很多这类常以双关形式化俗为雅的歌谣。由于我暂时没有时间通读《山歌》,所以,无法确认这首《答还山歌》是否脱胎于此。但是,无论它是在哪个时代成型,山歌创作的背景和初衷却是相似的,对个人自由和情欲的追求也是如一的。在这里,女性并未失声。我想,这就是真切的浪漫主义,它因人的存在而存在,永不消亡。
在当今现实世界里,山歌的“情欲”元素常常受人忽视。很多学者、政客为了职称、政绩纷纷举起“保护山歌民俗文化”的大旗,却对产生山歌的土壤避之唯恐不及。其实,“山歌”并不需要保护,需要保护的是人们“庸俗”的权利和表达“情欲”的自由。当滋养山歌的土壤不复存在,我们所听到的被定义为“山歌”的事物则与档案里书写的数字无异,只是对表达的不高明模仿。
让我们来看看笼中的金丝雀们是如何演唱这些被保护的山歌吧。在“艺考曲目列表”里,我们仍可以看到《啥鸟飞来节节高》的曲目。在演唱时,常伴随着强有力的钢琴、弦乐声部,演唱者通常是身穿长裙的女歌手,一边演唱,一边用她浓妆艳抹的五官尽力挤出官方钦定“农民式喜悦”的表情。要是关掉声效,你会以为是哪个东北农民在盼望丰收。
这种苏联式美声与样板戏结合而成的产物让我感到恶心,与这样的怪胎比起来,任何一个抖音、快手播主都显得读过几年书、受过点艺术熏陶。
这就是国家级的“保护山歌”成果,比不上法籍华裔导演作品里不过1分钟的一场戏。就在这个国家,人们普遍把艺术当做一种工具,而从未感受过艺术欣赏、艺术创作过程对感官和自我的冲击。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群体大谈文化、创新,我只能丢下一句“去你妈的!”
民歌《啥鸟飞来节节高》四眼母子的生存哲学
在这个国家,把艺术当做工具的人比比皆是。成绩不行,那就去艺考,把艺术当作生存保命的工具。在这里,他们不需要艺术表达,只是按照圈子的既定模式“努力地”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便有了上一节所写的东北农民版《啥鸟飞来节节高》。
如果理解了“艺术工具主义”,我们就不难理解《答还山歌》为何会被扭曲成这样的模样。对于这些人来讲,山歌的定义、本质、内涵、外延、音律、词韵统统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个——彰显保护山歌的成果。
在电影里,四眼母子就是坚定的艺术工具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在文革以前,巴尔扎克、大仲马、波德莱尔从来都不是文艺作品,而是进入某个圈子以谋生的工具;文革时候,它们又都是些不能被人发现的禁书。他们对禁书的保存,并非出于对文艺作品的爱护,仅仅是这片被反复凌虐的土地上人们谋生的本能——对保值物的青睐。
他们不相信知识和艺术,他们只是单纯地相信书籍可以作为保值物,在未来可以兑换成金钱,或是用来换取别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机会。文艺作品并未给他们的灵魂带来多少震颤,只是让他们多读了些字词,能借用别人的文字写一些阶级故事或社会主义打油诗——这就是保值物的附加值。
四眼母子也确实通过这样的附加能力获得了脱离乡村的机会,在成都的一个官方杂志社谋了份差事。只是,你不能指望他们通过阅读巴尔扎克或波德莱尔习得了创作伟大作品的能力。对他们而言,任务先于表达,政治先于艺术。
我曾听到过很多为这种艺术工具主义者开脱的言辞,无非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云云。在我听来,这些话都是狗屁。生存不是难事,人要维持生命,需要的东西本就不多,轮不到仅仅是为了活着就要糟践艺术。况且,他们那样,算是为了生存吗?不是,是谄媚,是为了向既得利益者靠拢。
我想,像四眼母子这样的人,是会在剧院为《啥鸟飞来节节高》鼓掌欢庆的。毕竟,他们是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他们需要的仅是装模作样进行虚假的表达,为职称和政绩欢庆。他们,是文明世界的鬣狗。
当然,我也不指望所有人在面临生活困境时能坚守艺术创作的操守。像四眼母子这样的人,只是芸芸众生的一种,他们的怯懦和精明都是能被理解的。只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原谅他们,但我绝不认同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为某种既定的“社会榜样”。相反,他们应当作为“现代生活英雄主义”的陪衬。当这些历史的尘埃褪去,显露出的应是那些无论在何种时候仍坚守创作操守的英雄。
基督山伯爵的意象
虽说作品名称强调的是巴尔扎克,但其他法国作家的作品也并未缺席。其中,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故事后半部分尤其重要的元素。对《基督山伯爵》有过了解的观众不难发现,叙事者马剑铃把自己、罗明、小裁缝分别带入了书中。对于马剑铃和罗明而言,小裁缝就像梅尔塞苔丝,是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而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唐泰斯和费尔南,即是友人,也是情敌。
从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剑铃在犹犹豫豫地些许扮演着费尔南的角色。他试图在罗明因故回家时修改阅读计划,另选了福楼拜、鲁迅的作品。他试图用同样的模式建立自己与小裁缝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仅仅作为替代罗明来给小裁缝读书的朗读者。只是,他的计划似乎不成功。小裁缝坚持“我还是更喜欢巴尔扎克”算是做出了拒绝。而后,小裁缝的怀孕也进一步打断了马剑铃的计划。
在原著小说里,叙述者“我”(马剑铃)的身份投射总是在唐泰斯、费尔南之间摇摆,甚至有更多如费尔南一般“背叛”行为的描写。此外,在小说里,马剑铃甚至与小裁缝开始玩起了表演的游戏。在小裁缝扮演起《基督山伯爵》里的梅尔塞苔丝时,马剑铃借唐泰斯的身份,短暂地享受着似乎他与小裁缝之间曾有过爱情的假象。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描写,它们让马剑铃的状态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享受唐泰斯曾有过的爱情,同时,他与后来的唐泰斯(即基督山伯爵)共享某种对小裁缝、梅尔塞苔丝不可得的惋惜。另一方面,这种游戏只是他趁着友人(兼情敌)缺席时的诡计,他扮演着唐泰斯,心中却怀着如费尔南一般的对自身罪孽的担忧和惶恐。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90年代末的天池
在千禧年前夕,趁着最后一波花岗岩热度冷却下来的时候,县城里的乡村道路已经修到了天池旁。哪怕是破旧的二手桑塔纳,也能在这条蜿蜒曲折的碎石盘山路上艰难攀爬,最终停靠在天池旁的一小块空地上。
这一地区的半山上,常有这样的一处坝子,将山脉划为两段,再往上走,垫脚的石板越来越少,直到只剩散落了一些脚印的羊肠小道淹没在密林里,要是不带上开荒的镰刀,很容易把路跟丢。
我似乎是98年时候在天池边玩耍过。那时的天池已经并不清澈了,不像有人会在里边游泳的样子。有农家把土豆装在竹筐里,荡在池边,据说这样就可以筐到鱼。在天池周围,还有一丛又一丛的竹林。差不多十株一丛,围着池子靠山的一侧散落着。在这些竹林间,又穿插着用石板铺成的路。这些石板像是页岩,宽大又扁平,一阶一阶地把重量压在彼此身上。
我在天池的时候,正遇上雨过天晴。空气里是落叶、虫豸腐烂的味道。太阳照耀过来,在竹林的泥地里投下了星星闪耀。石板都被清洗过了,雨水顺着石板的痕迹勾勒出它表面的高低纹路,又在太阳的照射下映照成银色的线条,随着微风轻轻抖动。
被雨水浸润过的石板非常好看,却也像好看的蛇蝎美人一样,从来没按什么好心,轻易就能把人摔倒。它们太光滑了,光滑得连青苔都不容易长。人在山路上摔倒时,周围没有任何可抓的东西——左侧是一道灌溉用的水沟,隔开了高大的玉米林,右侧是稀疏的竹林,竹子太远,竹笋太矮,都抓不住。就像电影里罗明背粪的时候,摔倒了,就没有东西可依靠。还要祈祷自己不要顺着山路滚下山崖,也不要侧身滚进一旁的水沟,更不要被粪水洒一身。
不要跌倒,不要用鼻子近距离感受撒落了粪水的山路,也不要在摔倒时惊到钻进干枯玉米杆准备冬眠的蛇——这是我从过来人那里听来的关于山野生活的忠告。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有把这些忠告听进耳朵去,很快就摔倒在这光亮的石板上,被裤兜里的玩具在屁股上扎了个印,还有一只绿色的四脚蛇,飞快地从我手背上爬过。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剧照谁是“小裁缝”?
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原著里,小裁缝的身份已经被弱化很多了,始终没有交代她的姓名。在电影里,她也不是荥经人,而是从天全那边来的。可惜,她的裁缝身份太过瞩目了,以至于县城里的人们只是稍加思索,很快就自作主张地公认了一位小裁缝的原型。确实如此,天凤乡只有那么点儿,天池旁也没几户人家,裁缝,也不多,还有谁呢?只是,当人们认定她的人生已囊括了所有这些艺术符号,她便成了一位在电影背后仍活在流言旋涡中的女人。
我还是不要再使用“小裁缝”这样的称呼了,这很别扭。在我的印象里,她是曾来我家做过帮工的裁缝阿姨。我从未想过,竟然有这样一天,我会在讨论一部电影时,从她的世界去看看县城女人们的人生,看看久不曾想起过的县城光景。
如果我没记错,阿姨在我家帮工时也有40多岁了,算下来,如今已是60多岁的人了。虽然人人都说她就是电影里的小裁缝,可她却没有小裁缝那么好的命。在电影最后,小裁缝离开了乡村,去了大城市,去寻找更多的可能。导演给了她一个好去处,说她去了深圳,又说她去了香港。可是,在现实里,在我所知的这30年里,阿姨仍是被困在这小小的县城里。
她也早不做裁缝了。在我家帮工时,那也不过是在县郊国道旁的山沟里,没出荥经县界。我曾听闻过她后来这些年的日子,就和很多离异的县城女人一样,要么做生意,有赚有赔,要么再婚,或是被男人骗了积蓄。
如今她也60多岁了,距离电影里那个小裁缝也越来越远。想着她,我便想起了电影里的老裁缝。在电影里,他去过雅安城,见过世面,在他的师傅家里见过小提琴,还能用不标准的英文勉强念出“Violin”。想想还真是讽刺啊。
山野里的爱与美
“小裁缝”的故事离我太远了,哪怕“她”或许也曾离我那么近。在我家那处农家乐,我曾切实地亲眼见证了一段山野里的爱情故事。如果在1971年的山野里真有过一段激烈的爱情故事,那我便见证了它的千禧版。当时我还小,只是隐约记得事情的一些经过。在这些见证者里,除了我家里的人,还有在这里帮工的裁缝阿姨。
我家还开着农家乐的那几年,除了裁缝阿姨,先前在奶奶家做饭的小保姆也在夏天做过一段时间帮工。我还是先说明白吧,她便是这段故事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则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厨师。我不确信他们之间是不是旁人嘴里明确的“恋爱”,我隐约记得,后来听说厨师在老家还有相好,没多久就离开了。
得闲时候,厨师和小保姆就会带着我和表姐在山里玩。厨师有很多新鲜玩意儿,比如用萝卜削一朵花,送给小保姆。这种花其实不难,削一些椭圆形的萝卜片,再用两根牙签十字交叉,把萝卜固定成花瓣的形状就可以了。我和表姐常常在分解花瓣结构的过程中把它给吃得精光。我们都挺喜欢厨师的,因为他好玩。那时候,还在念小学的我就明白了,讨小孩子喜欢和讨女孩喜欢其实是一个道理。
当我看到电影里周迅饰演的“小裁缝”时,我总会想起我在那个夏天看到的一切,总会想起那个小保姆。她当时年纪和“小裁缝”差不多,也就十七八岁吧。但和小裁缝不同,她长得,就像知识分子笔下农村女孩的范本:黝黑的皮肤,铮亮的大眼睛,乌黑的长发编成一股麻花辫。
我实在不想用这么公式化的形容去描绘这曾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活人,可我当时的记忆又很难想起她别的特征。要怪就怪时代吧,那时人们的审美总是那样单一,只会记得这样的女人。
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的笑非常特别。大多数人笑起来都会自然地半眯着眼睛,要是眼睛太小,笑起来就只剩一条缝了。她不一样,她笑起来时候也会睁大眼睛,脸上除了快乐,还有眼里的惊喜。相比起单纯的快乐,她似乎更享受这快乐带来的意外。
在我看来,这是她与周迅饰演的“小裁缝”最大的不同。虽然在电影里,周迅的灵气实在令人难以忘却,可是,这不是我所见过的山里姑娘的美。这个“小裁缝”身上混合了雅典娜的冰冷和阿芙罗狄的魅惑——这两位希腊女神连出生都极其“非人”,像是遗落在山间的珍宝,总是会离开这里。
而在小保姆身上,她的魅力更像是海伦,你在她身上能明确感受到人与神的交汇,还有两种力量的拉扯。她的所有外在特征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人类,可你却总能在一些瞬间从她身上察觉到神的惊喜。
周迅 饰 小裁缝垄断爱的解释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成功,并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山野里的爱情故事,而是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山野里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含混的故事,它以爱情的惨败收场,而这爱情的惨败却正是浪漫主义凯旋的号角,当这号角响起时,你却听见的是现实的声音。
如果仅仅是山野里的爱情故事,它并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文艺作品。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是,当爱情发生在山野的时候,似乎才更能刺激已丢了根的知识分子们麻木的神经。若仅仅是这样,那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用来满足知识分子优越感的猎奇故事。《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狠狠地给了知识分子们一记耳光。
当知识分子垄断了文字,他们也在试图垄断对爱情的解释。贯穿整个故事,马剑铃、罗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小裁缝灌输这种垄断的“文明”。可他们最终忘记了,爱与欲都先于文明存在,哪里由得了用文明去做出“最终解释”?
小裁缝的出走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她用行动告诉了罗明、马剑铃——我的美、我的灵魂、我的爱情、我的自由,都应由我的力量来塑造和解释。此时,雅典娜和阿芙罗狄的力量在她身上觉醒,她终于成为了一个断然与山里姑娘不同的女人。
由于小裁缝出走并非电影的结局,在这里,戴导并未有太多着墨。但是,在小说里,这就是故事的终章,戴导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两位青年追逐小裁缝的情形。有跌宕的心情,有崎岖的山路,有盘旋不已的红喙乌鸦,有遗失在风声里的告别。
在这场以失败告终的爱情追逐里,先前许多(有些并未在电影里出现过)人和事都胡乱地涌上来。所有这些象征都指向一个爱情故事的圆满结局,而眼前却只离别,甚至或许是再不能重逢的离别。只留下一句,“女人的美是无价之宝。”原著里写道,小裁缝变成一只小鸟飞走了,这样的描绘总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蕾梅黛丝升天的景象——在此刻,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对于马剑铃、罗明两位知识青年,这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他们自认与山民不同,自认与四眼不同,哪怕是在插队、做工,他们仍自认是巴尔扎克的信徒,是爱与美与自由的坚定拥护者。他们身上有知识分子的崇高、单纯、骄傲,也混有同样的虚伪、盲目、自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与小裁缝的关系是如锁链一般难以斩断的,甚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小裁缝看作自己的造物。而现实却是,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同样伟大而渺小。
正是小裁缝的出走,这个原本用浪漫主义笔墨描绘了许久的画卷终于定下了现实主义的基调。而且这样令人难过的现实主义结局留给人的却不仅仅是面对现实的伤感和悲痛。小裁缝走了,让两位知识青年显得那样渺小又无能,连一个人也留不住。小裁缝走了,也让他们显得那样伟大而有力,他们终究改变了她。
我想,这就是关于知识、艺术、爱与美的启示,它们不能让人完全克服自身的毛病,但仍能给人面对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即便是在崇高里夹杂了私心的知识分子,也有足够伟大的仅属于自己的使命去完成。
千禧年的落幕
在电影最后,戴导追加了回到天凤乡寻访小裁缝无果的部分,让往事都随三峡大坝淹没在水底。虽然这场后来新加的时代戏码将天凤乡迁到了三峡附近,可这场戏里的场景和人物,却仍像我故乡停留在90年代的人们。那些衣服,那些发型,那些农家胡乱堆砌的箱子和楼梯,都是那样熟悉。
根据资料显示,三峡第三期工程是在2003年开始启动,也就是说,居民的迁徙和安置在此前已经完成。据此可知,马剑铃应是在千禧年左右回去寻找小裁缝的。当我们回到现实,正是在2000年时,法国伽利玛出版社(??ditions Gallimard)出版了法文小说《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到了2002年,这部名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电影则成了第55届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开幕电影。
我不认电影最终的安排是一种巧合,相反,我认为,正是这样刻意的安排,这个故事才真正落下了帷幕。哪怕它不是足够优秀的电影,它却披着艺术的外衣将人重新拉回了现实。
就在艺术、现实的拉扯之间,就在这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之间,对过往记忆和艺术创作真伪的追问都无必要了。表述一旦完结,叙述人便再无垄断解释的权力。至此,只剩下观者的声音,只剩下观者在心中与自己的交谈和独白。
无论从电影里看到什么,人往往只会看到自我的经历。不如就安静地在这留白中臆想吧,什么也别说。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小裁缝”的故事:县城30年光景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影评”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