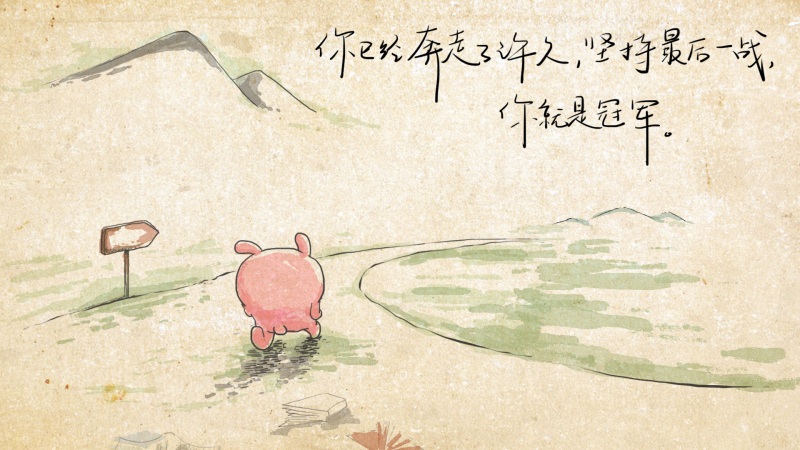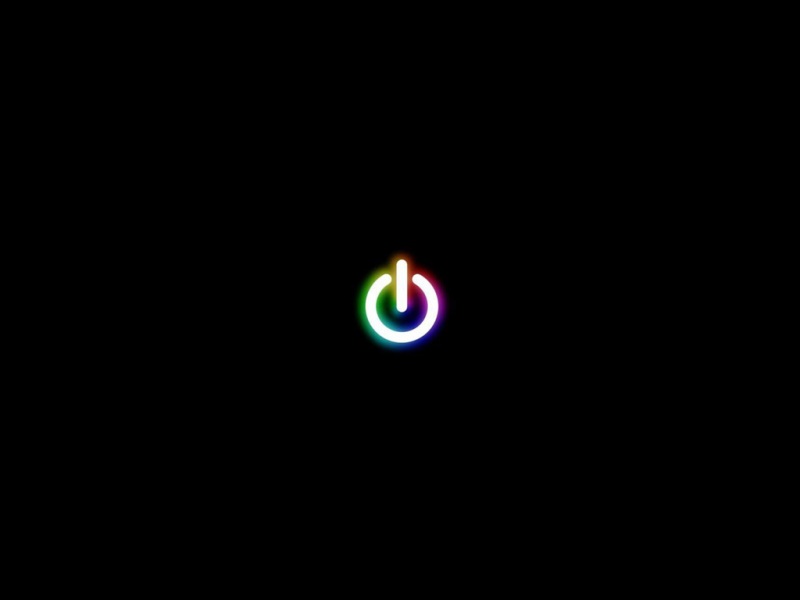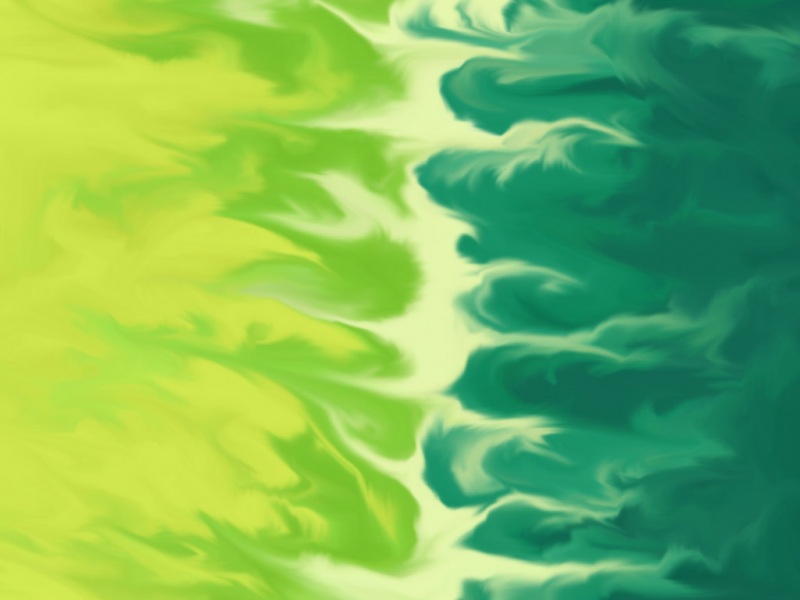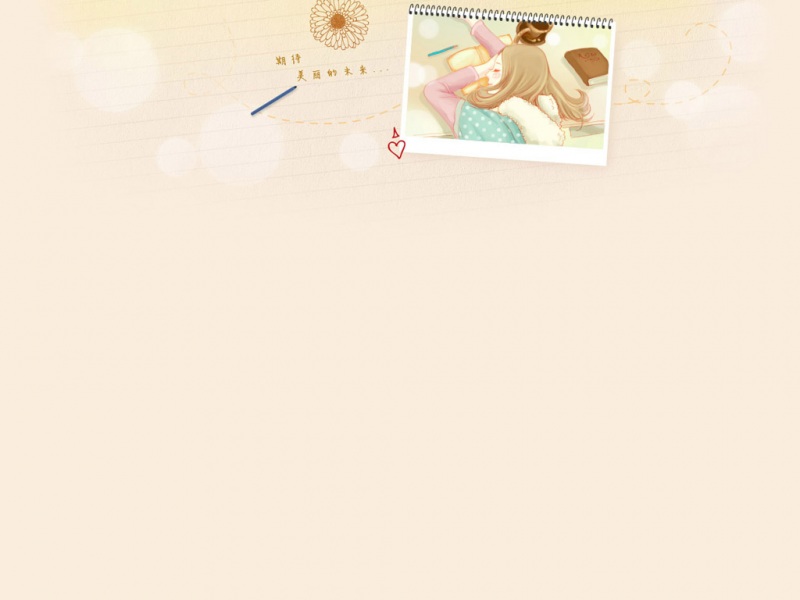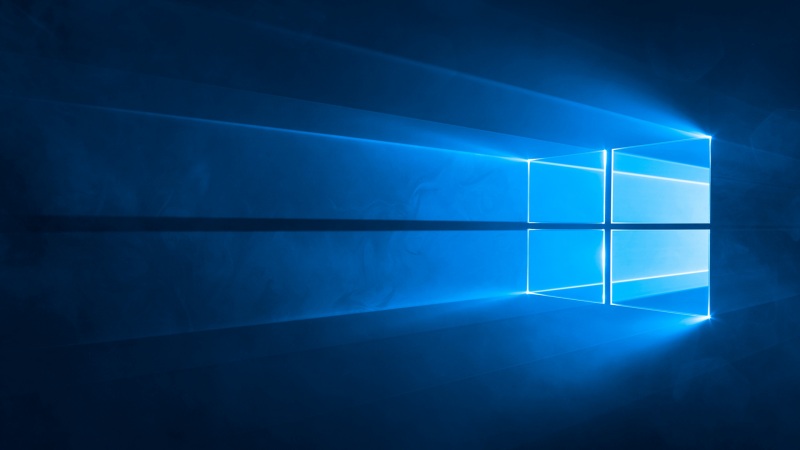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8280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7 分钟。
原标题:一个被自己的鬼故事“吓死”的人,当然,他还活着
澎湃记者 张维 实习生 邹佳雯 陈瑜思
全文约7800字,阅读约需15分钟
“14:20在酒店门口接你,给你叫了专车,车尾号是****。”张震的妻子兼经纪人小静发来信息,没有写上地点。
这次见面的开始像主角的故事一样神秘。
或许你不认识他,但也许对流传了十多年的传闻有印象——
2001年的一天,录音结束的张震从一堆小山似的粉丝来信中抄起当天的报纸,在第17版的一篇文章中赫然看到:“最近,在学生中传说,张震死了,被鬼故事吓死了。这是真的吗?”
一个讲“鬼故事”的人被自己的故事吓死,或许满足了一种关于传奇的想象,就像将军战死沙场,医生倒在手术台。
死讯当然不是真的。否则,故事就没有悬念了。
一
在沈阳的咖啡馆见到张震的第一眼,我脑子里立刻蹦出“可爱”这个词:他个子不高,一头卷曲的短发,圆圆的脸盘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背着双肩包渐渐走近,就像20年前他第一张专辑封面上的大男生。
《张震讲故事》发行的磁带、CD等。本文图片 受访者提供
20年前,张震风靡的程度大概可以类比当下的网游“王者荣耀”。一个曾在沈阳读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当年没听过《张震讲故事》,简直就是一种缺失。
“(害怕)不敢听,还想听”,恐怖程度不亚于从电视里爬出来的贞子。
1996年,辽宁电台成立娱乐台,鼓励主持人做制作人创办节目。张震那年23岁,还是大四学生,做了一档《张震讲故事》。
什么都讲,爱情故事,励志故事,还有恐怖故事。
那时,手机和电脑还是稀缺品,广播在校园中很流行。娱乐台有两种收听形式,一种是广播,一种是拨打电信电话99099付费收听,一分钟一块钱。每个故事多少人在听,听了多少分钟,非常直观。
统计下来,张震的节目总是收听率最高。而其中,恐怖故事最受欢迎。
“他那个节目有十几万分钟,如果一分钟一块钱,那就是大家花了十几万在听。”石代红是张震在电台的同事,比张震大一岁。
学生偷偷打电话听,月电话费从几十元暴涨到几百块;有的学生上课偷听被吓到,突然喊着:“老师!我看到我爷爷了!我看到我爷爷了!”很多家长为此打电话到电台投诉,还有人投诉到沈阳精神文明办公室,说张震的故事“污染精神文明”。
粉丝来信一麻袋一麻袋地运到张震的桌上。后来,爱情故事励志故事都成了过眼云烟,张震专心讲恐怖故事。
1997年,辽宁电台打算就《张震讲故事》出一张专辑,需要4个故事。张震没用电台编辑提供的,他自己创作了第一张专辑。
当时在沈阳北方图书大厦举办签售会,粉丝从全国各地涌过来,有的学生上课不能来,就让家长早早来排队。
据说现场安排了80个保安,图书大厦里全是人,木制桌椅都被挤坏了。张震被保安护送提前离场,就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简单跟粉丝见了面。
2017年张震在长白山。
二
同事石代红评价张震,“广播奇才,天生的脱口秀主持人。”有时直播没有备稿,张震就拎着本《读者》,也能讲的绘声绘色。
张震说,他打小喜欢听广播剧、评书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听完一段评书,就一个人扮演不同角色,比划念叨演一段。
他跟我谈起东北话的精准。边说边模仿,声音既浑厚又生动:比如,我想喝住你,东北话就是“站住!”“你干啥!”“你瞅啥!”“瞅你咋地!”“你说咋地!”
他表达能力强,普通话也标准,中学一直在学校广播站播音。那时赶上了粤语歌大流行,周四广播里谭咏麟的歌曲《朋友》前奏响起,紧接着就进来张震的声音,放音乐,念杂志文章,偶尔请人做访谈。
学校的老领导想要午睡,找到他说,你这样我没法睡觉啊,你这太吵了!“我就说,那你得找学生会,我们归学生会管。”
1993年张震考上了沈阳师范大学,念中文系。进大学不到三天,一个同学就打电话告诉他,辽宁省文艺台招业余主持人。他去应聘,就上了。
沈阳光荣街十号是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楼。现在,楼已用作它用,背后建起一栋崭新的大楼。
石代红形容,那是“古老的记忆”。在她有关20年前的记忆里,张震特别不修边幅,夏天常常穿个短裤T恤,趿拉着拖鞋就来电台。他经常成宿成宿录音,铺个军大衣就睡在办公室。
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石代红常听到张震在办公室里大喊,“哎呀,昨天录这个把我自己都吓坏了”。
跟如今写作一样,张震喜欢夜间工作,他说那样才有感觉。
点开《张震讲故事》系列中《剪刀》的音频,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从四周升腾起来,张震低沉浑厚的嗓音随着“咔嚓”“咔嚓”的剪刀声慢慢逼近。
“我非常膜拜声音的感染力。” 张震用声音给听众营造了一个神秘的世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你听到这句话就已经有预期了,我要赶紧让你的心理预期得到满足。”
他做过研究,人耳耐性有限,进入故事情节要快,集中。所以《张震讲故事》有声恐怖作品通常在15分钟左右。这样的故事,录音需要一天或者半天,后期音效制作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那时技术不发达,没有现成的音效,需要用巨大的开盘机(像旧式大大的磁带)来录声音制作。比如《剪刀》,他录了许多剪刀的“咔嚓”声,再后期处理加混响做成音效。
“特别不好弄,不好接,那会我们得听,有时候磁带在那儿转,停!”石代红回忆,最崩溃的是刚录好一盘带子,“啪”地就散了,那时心情无比悲催。
三
二十多年过去了。
媒介传播经历了巨变。《张震讲故事》从磁带变成CD,从CD变成手机增值服务,直到网络。
“死亡事件”被证实是谣传。他还在创作,只是作品从有声作品转向书籍出版、电影网剧制作。从2008年开始,他的长篇小说《失控》、《失踪》,故事集《牙印》和《头发》陆续出版。
2015年前后,以“张震讲故事”为素材制作的电影《张震讲故事之鬼迷心窍》、《张震讲故事之出租屋》和网剧《张震讲故事》也陆续上映。最近,他还正在修改一部写完的长篇小说,同时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和网剧剧本。
张震是个资深影迷,最喜欢的导演是希区柯克,最喜欢的恐怖电影是《危情十日》。当有人来找他做电影时,他充满期待。
他给《张震讲故事之鬼迷心窍》提供了三个原创恐怖故事,针对剧本给导演和编剧写了2万多字的意见,但没有得到采纳。
这部电影在豆瓣评分3.5,观众在底下评价,“烂片”、“看不下去”。
“只顾着去吓人,忘记了讲故事。”他也感觉失望。好的恐怖电影在他看来,是《危情十日》那种,“护士半夜进作家的门,突然一声闪电,一个仰拍她脸的画面”,“真正惊吓人的画面一个就够了”。
这是《张震讲故事》进军电影界的第一站,显然失败了。制作人于波认为,这让“张震讲故事”这个“IP”一开始就在减分。
一次电影落幕,接受完媒体采访的张震走在路上对小静说:“没有人知道我对‘张震讲故事’的野心有多大。”
“希区柯克女儿接受采访说,我父亲拍电影,他就不停在跟编剧磨本子。”他打算此后的电影或网剧剧本都自己操刀,因为觉得“电影成功在导演,失败在编剧”。
小静是张震的经纪人。他们没有公司,没有工作室,只有几个像于波一样比较固定的合作伙伴。她开玩笑说,“我们属于独立艺人”。
煤矿老板,文化公司老板,企业老板……都想找他们合作拍电影。但有两类人他们“基本不考虑”:一个是“自己都没有想好拍什么,就说钱够拍”的;还有一种,“恐怖片里没有古堡啊,盗墓啊,穿越啊,没有大场面我怎么投啊,你最起码要搭个地宫出来……”
靠谱的极少。曾有一拨人找到他们,说有个好的创意,但对剧本有个要求:一定要加上一个女鬼披散着头发在床上剪指甲的意象,“咔嚓咔嚓”。
张震觉得,恐怖电影给人一种错觉,让人轻慢它。“好多人受到热情感染,但一个意象距离故事还很远。”
夫妇俩强调,他们在等待“有缘的”、“合适默契”的导演,“遇不到,就很难做好”。
2016年张震在《张震讲故事之合租屋》电影发布会现场。
四
“有一个人走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总能发现眼前一个飘飘忽忽的白点在移动,这白点大概一人来高,好像有一个人戴着一个口罩。”这是张震最早创作的恐怖故事,叫“白点之谜”。
初中有段时间,每天午饭过后,十来个同学围在一起听他讲“白点之谜”,又害怕,又紧张。“白点之谜”到现在还是个谜,他说不清那时到底想说什么。只是觉得“你把别人吓到了,就很好玩”。
张震其实没有遇到过什么“灵异”的事。但他天然地关注消极的事,暗自期待庸常的生活突然变形,发展出荒诞的故事。
比如老师批评某个孩子,他会格外关注。“他哭了,我会偷偷看。可能这事儿过去半堂课或者半上午了,我还会观察一下,那个事情的影子还在不在。”
老师发脾气后还是正常上课,小朋友挨批评后还会去跳绳。但在故事里,张震会让这些生活小事沿着一条冲突的故事线走下去。
《剪刀》的故事灵感也来源于此。一天上午,张震在北京一家咖啡厅写东西,没什么客人,他靠着窗户,眼睛慢慢扫视咖啡厅:一个女孩坐在角落里。他观察人的兴趣又上来了。
如果这个女孩,突然站起朝他走来,会发生什么呢?他想。
“剪刀”这个意象突然蹦出来。他想象,她拿着剪刀扎自己的脸……这成了《剪刀》的开头。
人们习惯把《张震讲故事》称为“鬼故事”,实际上,他的故事里大多没有鬼。比如,第一部长篇小说《失控》,讲的是一个在现实社会里高尚完美的男人一步步被自己的欲望逼入深渊,最终死亡。
最初,听众们都以为是鬼在作怪,但到结尾,他总能圆满解扣, “哎呀,这个故事很可怕,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心”。
“厉鬼复仇”并不是他所热衷的,责任、爱,是他想要表现的东西。 “掰开了给你看,是毫不留情的。他让你看,这就是你。” 他喜欢希区柯克的作品里对人性的剖析。
《剪刀》讲一对姐妹,妹妹在给姐姐讲一个剪刀戳瞎眼睛的故事,姐姐深受折磨,但只能听不能反驳。原来,小时候姐姐不慎弄瞎了妹妹的眼睛,随着成长,姐姐的愧疚心慢慢褪去,但妹妹渐渐发现自己这一生都完了,怨念和仇恨在累积。
“你说,它有多么积极的主题,我不觉得。但人性有很多面,有好的坏的。正确的认识自己不就是正确的意义。”
他不想做“易碎的,一闪而过的东西”,希望将来人们想起一个故事,不用提到“张震”,“能讲到这个故事,就可以了”。
五
如今自由的创作状态,张震很满足。他把这归因于妻子小静,如果不是小静,他可能还在电台做主持人。
1997年,不满20岁的小静,来到辽宁电台。她跟着张震学习播音,俩人也合作录音——在张震的有声作品里,从小女孩到老太婆,几乎所有的女声都来自小静。
完成故事后期制作,张震常会让小静带上耳机,他敲下空格键,背过身,点起烟,边抽边观察小静的反应。
《盒子》是张震创作的第一个有声作品。那时他俩正在恋爱。他站在电台办公室窗户旁,兴奋地给小静打电话,跟她讲述《盒子》的“故事核”,一个人为了掠夺另一个人的财产伪装成了阴婆婆。
小静边听边觉得后背发麻,越琢磨越觉得害怕。这个是他俩合作录的,但小静从不敢单独听。有一次,她一个在家闲着没事,打开《盒子》,音乐起,还未听完,就吓得赶紧关了。
2001年,也就是张震被传死亡的那年,他的主持事业达到巅峰。除去电台职务,他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每月工资近9000元,而其他主持人只有两三千元。
他很有名,名片上只印有“张震”两个字,其余什么都没有。
那一年,电台外面的文化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说只需张震个人授权同意,就给他出专辑。此前,以电台名义出版的第一张专辑,收益、作品所有权并不属于个人。
他想把《张震讲故事》推广到全国,但这在电台有诸多限制,电台的工作也占据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
他想辞职,但从刚上大学就在电台工作,他又难以割舍。用同事石代红的话来说,像两个人谈了很久的恋爱要分手,“不是‘咵’一下就分开了,”分分合合好多次。
张震评价自己“附随性比较强,没那么勇敢”,他把最终决定权交给小静。
小静现在回想起来,忍不住笑自己“很傻很天真”,她有什么权利去决定别人的人生呢?
那时,她鼓励张震:“这件事你可以做一辈子。如果工作精力耗费太多,都可以不做,但要坚持创作。”
最终,他们都辞职了。“她积极鼓动我”,张震说话时,目光一直追随着妻子,“她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指引性。”
辞职不久,他跟几个朋友在饭店吃饭,遇到电台领导,他去敬酒。“我们头儿也是很幽默的,他说,哎,你干嘛来了?你扫地呢?”
六
从电台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人都以为张震还在上班。他继续在电视台兼职主持,维持一点收入,同时准备个人专辑。
《张震讲故事》是辽宁省电台栏目,其他很多省份无法收听。于是小静打算,在北京找面向全国发行专辑的公司。
她翻开电话黄页大本,找与音像出版有关的公司,一个个打电话。打之前,总要鼓起勇气,在心里默数到十,数完马上拨。
拨的第一个电话是中国国际音像出版社。她模仿当初两人的对话。“你好,我是《张震讲故事》的经纪人。”“谁?!”“《张震讲故事》,您知道吗?”“什么?我们不要!”
她又打。对话还是以对方“我们不做!”结束。电话黄页本没有带来任何收获。最后还是朋友向他们介绍了北京一家代理发行磁带的音像店老板。
小静向辽宁音像出版社申请版号,在沈阳生产,做磁带封面,加壳,向音像店运了5000套。小静说,这是他们离开电台后最艰难的一步。
磁带发行到全国后,CD时代来临,有北京的文化公司找到他们想给《张震讲故事》发行CD。
2003年7月1日,两人离开沈阳到北京。
这个时间张震脱口而出。两个一直在沈阳上学工作的人,第一次离开家乡。张震记得,他们租了一个货车,手忙脚乱地把家具搬上车,等到北京安顿好已经是半夜。
在北京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工作。张震在家埋头创作。小静寻找各种合作伙伴。
他们自己租棚、录音、制作,存款一直在减少,内心很忐忑。小静恨不得今天谈好了合同,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但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我跟三个人谈,也要一个周期,才能定下来拿到钱。”
小静对于张震来说,是经纪人,爱人,还是生活助理。每天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
他们住在北京东二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一大批白领从东直门地铁站下来,走进东环广场吃饭。有一次,小静正拎着大葱和鸡蛋从菜市场回家,和这群白领相向而行,突然一阵惆怅涌上心头。
小静过去是部队文艺兵,先天条件好,会唱歌,演过小品。离职前,她在辽宁电台的名气跟张震相当,主持的音乐节目非常受欢迎,电台老同事都记得她的开场白:“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DJ小静。”
离开电台后常有人给她推荐工作,她拒绝后向张震倾诉,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最终,她又安慰自己:“算了,总有一个人要为张震讲故事全心全意的坚守。”
为了生计,有一段时间,张震在北京一家电视台主持节目,评论社会话题,一个月拿1万多,一周录两次。
半年后的一天,他去录节目。没多久,就折返回家,沮丧地倚着卧室的门,说:“那个节目黄了。”正蹲着擦地的小静回头来了句:“黄了好啊!这回你没事干了,就专心写作了,晚上我们庆祝一下!”
七
石代红说,张震和小静,绝配。张震的高中同学李春凯也这么认为。
两人性格互补。小静乐观、爱冒险,张震不同,骨子里悲观。
2004年,张震的四姨去世,他给她穿鞋。四姨生前留学、任领导干部,是别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他在低头完成穿鞋这个动作时,脑中蹦出“悬念”两个字,他意识到四姨的人生,没有了任何悬念。
年纪变大,他常想到死亡。他对小静说“人生就是上帝的一个bug”:“你给它丰富的情感,但它终究会一无所有。你是一棵草,没有什么想法,大概也不想那么多。”
他的悲观投射到现实是世事无常,需谨小慎微。也许这就是他创作的源泉,张震讲故事的悲剧内核。
比如,他看到一座小平房上压着一个砖头,就觉得世界上最聪明的一颗大脑很可能就被一块破砖头砸死了。
张震的父母在沈阳铁路局工作,小时候他们一家人住在铁路局大楼背后的铁路家属楼,附近是铁路货运场、铁路医院、铁路学校。
他在铁路小学读书,学校后院的角落里有个大煤堆,和一个看门的老头。张震对煤堆感到好奇,但害怕占据了上风。对小孩子来说,所有看门的老头都是吓人的。
哥哥领他去看电影《画皮》,他听说是恐怖片,犹豫不决。后来去了,灯一黑,音乐响起,他马上就跑回家了。
长大之后,哥哥的同学去世,他去送葬。遗体火化时,他想去卫生间,卫生间靠近存放骨灰的地方。他看到骨灰架子,一步都迈不动,憋着尿跑回来了。
他现在44岁,依然胆小。女儿悠悠养了一只兔子,晚上放在花园的笼子里。兔子动起来快,可以瞬间180度转弯。他常被惊吓到。
他待人接物也谨慎低调。在石代红印象中,他很少跟同事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打算从电台辞职的想法也几乎没有跟小静以外的人提起过。“跟朋友一起开玩笑很张扬。但是在一大群人中,不是那种特别职业、会运筹帷幄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
张震跟高中同学李春凯因为个性相似成了多年好友。李春凯说,张震从不会主动向朋友提要求。他考了驾照,却不敢开车。有时李春凯帮他开个车,张震就会觉得特别麻烦对方。
一个这样“胆小”的人却创作出那么多“吓人”的恐怖故事,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张震也常自我分析。他总结,自己胆小,却又向往神秘。
沈阳铁路局和家属楼中间有一大片灌木丛,郁郁葱葱,树高及人。张震常跟小伙伴们从后墙翻进去,玩藏猫猫儿,或者摘“天天儿”吃,这是一种红色野果子,小而圆。灌木丛的未知诱惑着他,老在他脑子里、梦里出现。
铁路家属楼,邻居间住得很近,哪家有人去世,就把花圈摆在门前,许多人进进出出。张震看到花圈时总会有点小小的兴奋,他会格外留意。
回家后他就想象那家人在做什么,去世的人还在不在屋里。他问家里人,邻居为啥死了。死者家人哭得特别夸张,他问大人,为什么要那么哭。
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却对它散发出的阴暗气息充满好奇。
八
采访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他一边跟我对话,一边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有时,我们聊天被小静打断,他也会停下来耐心等待。
张震显得谦卑且富有耐心。他说话时总是认真看着对方的眼睛,闪动着真诚和渴求。尽管比我年长许多,但在我们交谈的11个小时里,他一直用“您”称呼我。
在悲观、谨小慎微、低调谦恭的张震之外,还有另外的他。
主人公称自己是个在生活中极具幽默感的人。小静也说他每天都一个人逗的乐到不行。石代红也觉得张震“很逗逼”。
他极宅,不用手机,我跟他联系时都是通过小静。没有手机对他来说烦恼只限于不能骑共享单车。他依旧每天看各种,走哪儿都爱观察人。
《失控》那部小说与QQ有关。为了写作,他特地注册了QQ,每天挂着,跟身边的人聊,也跟研究技术的朋友聊。
小说结束后他就再也不用QQ了。他还是喜欢与人面对面聊天,看别人的表情、状态时,就会去想,“ta有什么故事”。
2017年北京,张震、小静和他们的两个女儿。
2015年,人们发现他开了微博,身份认证是“作家”,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为了经常回去看女儿,张震在北京和沈阳两地轮流居住。相对于北京,他更喜欢在沈阳写作。那里节奏慢,安静,不会被各种各样的饭局打扰。
写作时,他有着一些小癖好:指甲长一点必须马上剪,因为无法忍受指甲磨到键盘的感觉;他还喜欢听音乐,要先选好歌单。
他一般构思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需要一周,构思时常深陷其中,“后半夜起来倒水时自个跟自个说话,一边接水一边说,这…不对,他不可以到那儿,他应该到那儿。”
“好多次我让他等我,我就看他来回走,这样……”小静惟妙惟肖地模仿张震构思作品失神时的奇怪动作。
小静是张震的第一个读者。但他只会在作品完成后给她看。“我每次在邮箱里接到他的故事,就特别兴奋,舍不得快点看完。”小静躺在床上看时,张震就在旁边忐忑地等待着。
他在微博上跟网友分享跟家人的生活。成为父亲后,张震觉得自己变化很多。“得让自己正派起来,不能太散漫,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有个怪模怪样的爸爸。”
在沈阳时,他早上6点半起床给女儿做早饭,然后等她去上学,再给自己泡杯咖啡,开始写东西。
他原本是个特别需要独立空间的人。创作时如果门开着,就没有安全感。但女儿是个例外——他总是一呼百应。“小一(张震的小女儿)倚着门,喊,不给糖我就捣蛋!不给糖我就捣蛋!我就偷偷站在门后,她就特别高兴地透过门缝看。”
今年8月4日,是张震和小静结婚10周年,他们在北京跟几个朋友一起庆祝。“我当时还哭了一鼻子,我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让我生活的这么快乐。”
这就是作家张震在人间的生活。他的大女儿悠悠已经8岁,偶尔也会即兴讲个吓人的故事。那是一个奇幻的故事,里面有公主,有火龙。
想听张震与鬼的故事吗?戳阅读原文,张震在澎湃问吧等你来问!
本期编辑 邢潭
责任编辑: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一个被自己的鬼故事“吓死”的人 当然 他还活着”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